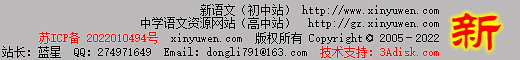这个8月,对于余华迷们来说,至少有两个好消息,一是作家余华终于“迷途知返”,重新开始写长篇小说了,并出版了自己的最新小说《兄弟》;二是今后的五年里,余华要在家里老老实实写小说了,他希望自己能“多写几部长篇小说出来”。
余华新书《兄弟》的上半部分,将在今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亮相——这显
|
然是个不完整的亮相,因为直到今年的11月,这部余华自认为是自己“写作生涯中最厚重的作品”的下半部才能出版。
在书店里,《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始终位于热门“畅销书”行列。从1996年到现在,在接近10年的时间里,余华只写随笔,或者四处游荡。这个被称为“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的人,始终不肯交出自己的第四部长篇小说。
他的“任性”,令人不禁要猜测:余华10年下的“蛋”,究竟什么模样?是什么原因让他“荒废”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又是如何“活着”的?《外滩画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对余华做了专访。
《兄弟》:并非10年下的一个“蛋”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这些年,圈子里都传说你在弄一个大部头,现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请介绍一下这个新生儿——关于它的名字、篇幅、时代背景、故事内容,以及表达方式等等。
余华:那部大小说是五前开始的,一直写得不顺利,前年去美国住了七个月回来后,也就失去了写它的欲望。去年4月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就是这部《兄弟》,刚开始打算写10万字,后来失控了,写了40多万字。这是由两个时代相遇后产生的故事,前一个是反人性的“文革”中的故事,后一个是现在的人性泛滥的故事,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却发生在同样的人身上,这是我写作《兄弟》热情所在。
外滩:我记得你在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说自己找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一种韵律,那是越剧的韵律。我很好奇,这次你会用什么韵律来写?
余华:因为《许三观卖血记》是通过对话来完成的,这样对话就不单纯是人物的发言了,同时还是叙述的推进,所以人物的对话需要韵律。这部小说已经不能用“韵律”来解释叙述的风格,我想应该用“众声喧哗”,尤其是在下部。
外滩:据说这次的作品在出版上也很不同——8月出上半部,年底才出下半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罕见的出法?
余华:全书有40多万字,上部18万字,下部接近30万字。上部先出版是为了配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今年8月的上海书展是文学和艺术的主题。
外滩:这么巨大的作品(至少目前看来从篇幅上是这样的,而且用了将近10年时间),在你的写作生涯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若让你预测,它在整个文学史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余华:没有用了10年,我96年到99年都在写作随笔,2000年开始写作一个世纪的故事,写得很不顺利,2003年8月去了美国,住了七个月,回到北京后就没有继续写作下去的欲望了,去年4月才开始写这部《兄弟》,一年多时间写了40多万字了。我想这部作品在我自己的写作生涯里,应该是至今最为厚重的一部。
外滩: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你是公认的作品较少却几乎没有废品的作家,原因是你从来不肯重复自己,这次的作品和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
余华:第一:我正面去表达时代的特征,以前的作品都是背景;第二,叙述的强度增加了,以前只能叙述几千字的段落,现在叙述出来会有几万字。
外滩:写这个作品的过程中,最痛苦和最兴奋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余华:最兴奋的是我写了3万字左右的时候,叙述就控制我了,这是最好的写作状态。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始,是作家在控制叙述,写到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应该是叙述来控制作家了。我这次差不多十分之一的时候就被叙述控制了,这实在是太美好了。
最痛苦的是写作时的失眠——因为睡眠不足,想写作可是没有状态,感觉就像是想进饭馆吃饭,可是口袋里没有钱一样。
外滩:你写作很多年了,能不能总结一下自己各个阶段的风格。
余华:让评论家来总结吧。
写随笔就像是听音乐
写小说那是经历人生
外滩:大约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吧,你都很少露面。关于你的消息,多半是从国外媒体折射回来的。请谈谈这些年你的“外事活动”。
余华:“外事活动”确实过分多了,今年一月我刚换了一本新护照,旧护照上已经没有空白处了。我对自己的新护照有个规定,五年期限里只能往上面贴五张签证,意思是今后的五年我要在家里老老实实写小说了。“外事活动”就是游山玩水,吃吃喝喝,对着外国人说中国话,中间还要夹着一个翻译。
外滩:在这个趋利时代,文学已经越来越接近边缘。问一个敏感的问题,你靠什么生活?
余华:靠版税生活。
外滩:不出门的时候,你每天是怎么过的?具体说说你的时间表。
余华:如果睡好了,我就可以好好写作,如果没有睡好,我就无所事事,上网看电视,或者继续躺到床上去,看看能不能碰上运气睡着了,这样晚上又可以写作了。
外滩:有很长一段时间,您都在写随笔。而那些随笔中很多都是对各领域里的大师的重新阅读,那是你的一个休眠状态吗?
余华:应该是一种梦游状态,很美好。
外滩:写随笔和写小说,对于您来说,有着什么样不同的感觉?或者说,对您整个的写作,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余华:写随笔像是听一段音乐,看一场电影;写小说,尤其是写长篇小说,那就是在经历一种人生了。
外滩: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对于你来说,写作意味着什么?
余华:写作让我觉得人生完整起来,每个人都有很多欲望和情感,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表达出来,写作可以让这些在虚构的世界里尽情表达。
外滩:如果不从事写作,你认为自己会去做什么?
余华:还在拔牙。
以前是“活着”,现在是“兄弟”
外滩:批评家谢有顺说:“余华作为一个作家的重要性,是因为并非每个作家都能让读者如此挂心他的写作计划的。”他认为同时代作家中,你是写作字数最少的作家之一,但也是废品最少、被研究得最充分的作家之一。作为一个优秀作家,你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这是文学界包括世界文学界对你的评价。那么,你对自己是如何评价的?
余华:我觉得自己从事作家的工作,确实干得比一个牙医好。
外滩:很多年以前,人们说“残酷的余华”。人们说死亡、暴力和血经由余华的叙述,被指证为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和内在本质。时间过去很多年,你当初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吗?
余华:我对世界的看法总是不断在变,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同的时期写下了不同的作品。
外滩:你曾经说过,“好读不等于轻浮。我们的纯文学作家自己让路给通俗文学作家,使他们的地盘越来越大。”这是否意味着你将在“纯文学”和“好读”间搭桥梁并有所建树?
余华:我忘了自己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我想文学不应该有“纯”和“通俗”之分,文学就是文学,伟大的,好的,一般的,坏的,坏透了的,如此而已。
外滩:你关注外部世界吗?你的表达是否因为这个世界的不断变化而变化?
余华:是的,我很关注,不是为了写作去关注,是为了生活去关注。
外滩:你的小说《活着》是最早被搬上银幕的一批。小说被拍成电影,无疑扩大了它的知名度。未来还会有哪些你的作品被拍成影视作品?很多作家对此显得不以为然,你的态度如何?
余华:我欢迎自己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
外滩:在中国文学圈你最欣赏的作家是谁?在世界范畴你最欣赏的作家是谁?为什么?
余华:太多了,我都可以把这些名字编成一支军队。
外滩:说你喜欢的上海作家的名字以及原因。
余华:王安忆和陈村。
王安忆的优秀有目共睹,不用我来说;陈村的优秀是他的“坏”,前年他还在告诉别人,“余华根本没有写小说,他是骗你们。”我喜欢他。
记得有一年全国作代会,大会表决的时候总是一致通过,这时陈村就站起来了,举手投出弃权票,他的理由就是不让大会决议一致通过,有一个弃权的就不能说一致通过了。散会后,他弃权的右手红得发紫,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握一下他的右手。
外滩:说一个你最喜欢的汉语词汇。
余华:以前是“活着”,现在是“兄弟”。
朋友本来不多, 现在仍然不多
外滩:除了写作,你还有什么样的个人兴趣?你花多少时间给自己的“业余爱好”?
余华:高雅的是听听音乐读读书,世俗的是上上网看看电视。
外滩:通常什么事情会令你焦虑?什么事情会让你无比放松惬意?
余华:睡眠不好让我焦虑,睡好了让我无比放松。
外滩: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重要的人物,他们或许带给他幸运或许带给他安慰……你能说说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吗?为什么?
余华:当然是我的父母,没有他们,哪有我?
外滩:我曾经听很多男人说,到了中年,才发现老朋友越来越少了。你在生活中的朋友有几个,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值得你珍惜?
余华:朋友本来不多,现在仍然不多。
外滩:对你来说,生命当中,哪些是可以舍弃的?什么又是必须坚守的东西?
余华:拔牙是可以舍弃的,写作是必须坚守的。
记者手记
他居然用了个惊叹号
大约是1997年吧,有一天,一位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拜访余华,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更早的时候,我的周围充斥着一堆余华迷。其中一位仁兄,甚至能背出余华所有的早期作品。在一次给我的信中,他居然字迹工整地抄了一遍《此文献给少女杨柳》,附在信的后面。所以那个时候,我虽然几乎没有读过余华,但他在我的印象中已经是“偶像派”了。电影《活着》解禁的那一天,朋友们一边流着眼泪看片子,一边喝酒庆祝,通宵达旦。
坐电车又换地铁,我们费了好大的周折,终于在下午赶到余华家。和北京的大比起来,余华家局促而昏暗,白天也得开着灯。门外堆满了各种文学期刊,有一些还没有拆封。我暗自想,文学青年们只要扮作收废品的,就可以不必跑书店就能低价获得最新最全的文学期刊了——90年代,文学虽然在向低迷滑行,但比起今天,仍然有大量的狂热分子。余华就坐在电脑前,他的周围,书籍泛滥成灾。
那个时候,余华还住在总政的家属区,他的太太陈虹当时在总政做一名编辑。我的朋友悄声向我介绍说,陈虹是余华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时的同学,写诗的,在作家班的时候,陈虹比余华有名气。这位四川女诗人,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之一,温润而从容。他们的儿子余海果,很内向的样子,黑色的眸子,闪着冰冷的光芒。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余华,关于他的消息,多半是从国外媒体的朋友那里听到的。今年上半年,我发了个短信给他,问他新小说什么时候出来。他回说,下半年。我问出来后是否可以第一时间采访,他回说,当然可以!
他居然用了个惊叹号。(记者 俞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