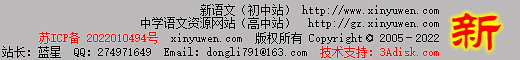即使《兄弟》达到了《许三观卖血记》的水准,它依然是失败的。读者花更多的时间阅读,书架上也占用了更多的空间,两者所能提供的却相差无几,被淘汰的显然是笨重者。
他(余华)还提到很多段落都让自己哭过,一边掉泪一边写作。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两种传奇的真实性,可是对传奇背后隐藏的某种逻辑不以为然。……失控和哭泣不是经典的专利,在刘作家、赵诗人之类文学青年的写作和阅读生涯中也一定不会缺少这种传奇。
从头到尾,讲故事者的身份一直模糊不清,充满内在的冲撞,声音非常杂乱却绝非什么“复调”,叙述毫无节制却绝非什么“狂欢”。
《兄弟》上册刚刚出版的时候,我曾在网上看到前两章的电子版。可能是不习惯在网上阅读长篇小说,或者有其他事情耽搁,当时只读了开头就没有继续下去。这次读完《兄弟》上册已是半夜三更,竟然有些期待,联想起余华受到的“围攻”,顿时打算“见义勇为”,准备读完小说撰文为他辩护。一觉醒来,拿起《兄弟》下册,读着读着终于倒戈,动起“投井下石”的念头。尤其读到宋钢去做丰胸手术的时候,惨不忍睹,不是情节悲惨,而是小说不忍卒读。几乎要弃置不顾,只是考虑到一个评论者的“职业道德”,才把整部小说读完。
在横轴和竖轴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兄弟》是一部“失败之书”。在把《兄弟》称作“失败之书”之前,需要说明我打算把这部小说放在何种坐标里。《死亡诗社》里出现过“坐标批评”:把诗歌艺术性的得分画在图表的横轴上,把它的重要性记在竖轴上,计算一下所覆盖的面积,得出它的优劣;基丁老师对此深恶痛绝,让学生把这一页课本撕掉。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是这次准备顶风作案,以作者为横轴,以作品为竖轴,只是不再采取计算“覆盖面积”的评价标准。
首先,横轴上的作者是已经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作家余华,不是海盐牙医余华。面对批评,余华大概很委屈,为什么评论家会放过其他明显不如自己的作家,把炮火倾泻在《兄弟》上。毫无疑问,在每年的几百部长篇小说中,《兄弟》至少也是中上水平。但是,对于一个推动了汉语写作的作家,评论家有理由提出比对一个文学青年高出许多的要求。《兄弟》里的赵诗人仅仅在县文化馆的油印杂志的夹缝里发表四行小诗,一跃成为刘镇名人。如果以刘镇的标准衡量《兄弟》,把它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著”也不为过。但余华一定志不在此,《兄弟》面对的是整个中国的读者。与其说批评者看低了余华,不如说是称赞者把余华放在了一个较为狭小的坐标里。称赞一个成熟的写作者“有潜力”,如同称赞一个不太漂亮的女性“有气质”,多半是没话找话,安慰为主。正是如此,《兄弟》的位置非常尴尬,它难以代表汉语写作与其他语种写作进行对比,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其他具有可比性的国产小说。有评论家看到《兄弟》想起铁凝的《笨花》,这种超级链接很有创意,却让人不敢恭维。让他们两位互相学习,最后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踏着舞步而来,各自爬着回去。我更愿意把《兄弟》放在余华自己的写作谱系里,当然,这不意味着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标尺刻舟求剑式地测量这部新作。
其次,竖轴上的《兄弟》是一部字数多达50万字的超长篇,不是一部10万字的小长篇。有人看不起短篇小说,认为只有写出长篇小说才是大师,这种“文体歧视”跟种族歧视一样荒谬,它最后简化为“篇幅歧视”。在《兄弟》里,刘作家发表的小说密密麻麻占了油印杂志的两页纸,就比赵诗人气派多了。这种“以篇幅论英雄”的习惯不是刘作家的专利。记得前几年另一位刘作家推出四大本《故乡面和花朵》,被誉为中国的《追忆似水年华》,除了厚度相似,我看不出刘震云和普鲁斯特有什么联系。一部作品的品质不能由它的字数所决定,它需要拥有与体积对称的容量,否则就会成为电影《佐罗》里虚胖的中士,体积庞大但是重量有限。书籍的厚度非但不能保证作品的深度,反而促使人们对它提出更高的要求。一部身材庞大的小说占用了更多的资源,自然需要释放更多的能量。即使《兄弟》达到了《许三观卖血记》的水准,它依然是失败的。读者花更多的时间阅读,书架上也占用了更多的空间,两者所能提供的却相差无几,被淘汰的显然是笨重者。如果刘作家的《故乡面和花朵》压缩成一本,没准评价会更好一点。
两种“传奇”
在这个坐标体系里,作者的身份和小说的篇幅都促使评论者用挑剔而不是更宽容的目光打量《兄弟》。余华本人对这部小说已经足够宽容,他毫不吝啬地动用了大量的褒义词,称这是自己“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我更愿意把这种“自我表扬”理解为商业需要,为了配合小说销售故意夸张一点,对此不必苛责。可是他多次渲染写作过程中的“失控传奇”以及阅读过程中的“哭泣传奇”,却值得具体分析。
余华提到《兄弟》和《许三观卖血记》都是在失控的状态下写出来的,构思中10万字的《兄弟》最后写作时超过50万字,本想写成短篇的《许三观卖血记》最后写成长篇。他还提到很多段落都让自己哭过,一边掉泪一边写作。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两种传奇的真实性,可是对传奇背后隐藏的某种逻辑不以为然。余华把“失控传奇”解释为“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仿佛暗示着作者被灵感附身。“哭泣传奇”对“失控传奇”进行再度认证,一般而言,感动落泪是对一部作品最为常见也是最高的评价。这两种传奇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它们从写作和阅读两个层面赋予作品以神秘性,从而确认作品的经典地位,正如每一位成功人士都会津津乐道自己出生时的雷电交加。其实,传奇对于经典既不构成充分条件,也不构成必要条件。“失控”和“哭泣”不是经典的专利,在刘作家、赵诗人之类文学青年的写作和阅读生涯中也一定不会缺少这种传奇。余华有一个精辟的说法,即某些作家“不描写内心,专描写内分泌”。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失控传奇”有点像内分泌失调,“哭泣传奇”更像外分泌失调——这只是一种文学隐喻,不是医学处方。
谁在讲故事?
在迂回包抄之后要对小说发起“正面强攻”,我打算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地讨论一下叙述者的问题。在一次访谈中,余华特意提到《兄弟》不是一部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是“我们刘镇”叙述的小说。在阅读过程中,我也一直纳闷谁在讲故事?余华的说法没有解答我的问题。小说中确实多次出现“我们刘镇”,但是叙述者究竟是“我们”还是“刘镇”呢?“我们”是一种集体目光,视力范围限于公共事件,大街上李光头的“示众”、桥头上宋凡平的“漫卷红旗”、公共汽车站的“屠杀”都可以成为注视对象。但是,《兄弟》还有“我们”视线之外的诸多情节,新婚那天凌晨李兰坐在床沿看着黑夜如何消散、宋凡平带着两个儿子在夜晚去看大海,这些幸免于集体目光因此得以残存的温暖秘密怎么可能通过“我们”来叙述呢?
不仅叙事对象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兄弟》的叙事方式也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赵诗人和刘作家是刘镇的两大才子,《兄弟》的叙述者胜过他们不止一筹,难道是隐居在刘镇的世外高人?在另一次访谈中,余华“辩证”地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他先是否认李光头、刘作家、赵诗人或余拔牙身上有自己的影子,然后又表示“每一个作家心中都有非常多的人物,每一个又都可能是自己”,进而称:“我发现了李光头、宋钢、童铁匠、苏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妈也是我自己。”可是,整部小说都没有理顺“我们”和余华之间的关系,两种叙事方式打成一个又一个死结散落于小说各处。“我们”本来应该在余华的控制之中,却常常被小说中的人物劫持。
小说开篇便是李光头偷窥女厕所被赵诗人活捉、揪着游街,后来刘镇的男群众包括赵诗人为了知道细节纷纷请李光头吃三角五分钱一碗的三鲜面。延宕可以唤起快感,赵诗人打断了“偷窥”,李光头中止了“口述”,却唤起了全镇男群众的快感,先是道德快感、然后是性欲快感,合在一起就是有道德感的性快感。吊诡的是,余华戏谑着刘镇男群众的集体心理,“我们”却沉浸到快感中不能自拔。虽然“偷窥”被打断,关于偷窥的“口述”却重复了至少56次;虽然“口述”在关键处中止,关于口述的书写却一发而不可收。叙述者对细节的着迷,与李光头、赵诗人以及刘镇男群众的表情高度一致,“我们”一边口干舌燥,一边竖起了耳朵。
鲁迅《祝福》里的“我”是一个回乡的出门人,与祥林嫂和鲁镇若即若离,叙述者的游离身份使“我”避免陷入祥林嫂的叙述快感和鲁镇的听觉快感。《兄弟》里的“我们”却表情暧昧,被自己所讲述的故事陶醉,“失控传奇”正是陷入叙述快感的表征、“哭泣传奇”则是陷入听觉快感的表征。这一点在《兄弟》上册的其他部分有所节制,这跟主题转向暴力有关,但是在《兄弟》下册再次蔓延,有过之而无不及。小说结尾处提到绰号“祥林哥”的王冰棍,他日复一日地用电视频道追踪余拔牙的踪迹,日复一日地向别人讲述余拔牙的传奇。“我们”同样感染了“祥林哥”的症状,字数从10万扩展到50万,正是在过度享受快感之后出现的叙事“浮肿”,《兄弟》下册的厚度是上册两倍也就不足为奇了。欲罢不能的写作状态,不一定是灵感附身,更有可能是“祥林哥”附身,与其说叙述者失控,不如说他被叙述对象俘虏。
如果说叙述者是“刘镇”,是否会缓解这种症状呢?余华已经否认了这种第三人称叙述,《兄弟》的叙事对象也超出了刘镇的管辖范围,李兰住过的上海医院、宋钢周游过的福建、广东、海南,都不属于刘镇的地界。《兄弟》的问题不在于叙述者是“我们”还是“刘镇”,两者都无法克服前面提到的种种障碍。小说采用了“我们刘镇”这种有限叙事的视角,讲述的却是一种全知全能叙事,这种背离是《兄弟》失败的症结所在。“我们刘镇”仿佛具有特异功能,可以深入李兰、宋凡平的卧室,可以远赴海南;一会像赵诗人眉飞色舞,一会像李光头卖弄噱头、一会像李兰满怀深情、一会像“祥林哥”喋喋不休。从头到尾,讲故事者的身份一直模糊不清,充满内在的冲撞,声音非常杂乱却绝非什么“复调”,叙述毫无节制却绝非什么“狂欢”。
最后需要重申,我把《兄弟》称作“失败之书”,是在一个苛刻的汉语写作的坐标背景下,没有彻底否定的意思。我更倾向于腰斩《兄弟》,即上册删除前两章构成《兄弟》A,上册前两章和整部下册重组成《兄弟》B。这两个部分除了主人公的名字相同,看不出有什么内在关联。《兄弟》A的字数接近余华构思中的10万字左右的小说,重复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风格,不会让人太过失望,但除了饥饿、刑罚和温情,也没有出现新的元素。《兄弟》B倒是提供了新的可能,它更适合另一种坐标,苏童称之为“畅销的纯文学”,我更愿意把它看作“精致的通俗小说”。“三角恋爱”(李光头、宋钢、林红)的骨架,配上略有文人色彩的口语,不仅为刘镇群众喜闻乐见,也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李光头求爱的情节类似于《有话好好说》的镜头,只不过女主角一个叫林红,一个叫安红。余华的转型,重走了张艺谋、陈凯歌的转型之路,在四面楚歌中赢得票房。这是不是一次华丽转身?我们不妨静观其变。 (王晓渔)
(编辑 小题)
相关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