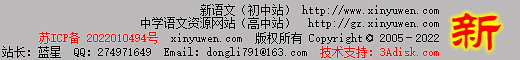记者:是不是少数民族容易把好多事情想得简单?
阿来:也不一定,少数民族入世的人多得很。我觉得还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吧。其实也是一个个性问题,不一定是后天的修为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基本上是一个宿命论者。宿命论从积极方面来讲可以支持你:就是这么几十年,精彩一点,丰富一点,一辈子当成两辈子、三辈子来过。另一方面,它又导致你很消极:就这么几十年嘛,你著作等身又怎么样,你
三十岁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一个诗人诞生了,帝王、巫师一般穿过草原
记者:我喜欢读你那本《大地的阶梯》,并试图从中找到你精神的来路。我看到你在里面写:“不一样的地理与文化对于个人来说,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启示与引领。我出生在(嘉绒)这片构成大地阶梯的群山中间,并在那里生活、成长,直到三十六岁时,方才离开。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片大地所赋予我的一切最重要的地方,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
阿来:当然肯定会发生一些外在的变化。但从本质上来讲,它变化的这个性质和方向,其实已经确定了。所以我确实不焦虑。如果你研究过我的诗集,你会发现。我年轻时代写给自己的诗中有两首对我很重要,差不多决定了我后来的文学走向,一个是《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
记者:诗集的第一篇。另一首应该是《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
阿来:对,那个完全是心情的实写。30岁那年我就徒步在那个草原上漫游,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出了第一本书《旧年的血迹》。
记者:但是好像出完了以后你很焦虑。
阿来:都不只是焦虑,而是很恐怖。所有人就开始叫你作家。惯常的做法是这些人就跑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拿着这本书找专家、找所谓这些名作家、批评家推荐,然后就急于混到这个文坛当中去。而我当时很焦虑的不是说我能不能出名。
记者:你觉得不够好?
阿来:第一是觉得不够好,第二个是,我真的可以做这个吗?因为当时我对文化人有一个很强的批判心理,我甚至很刻薄地想:“我会不会写写写,就写成一个县城的、地区的什么文化馆的馆员终其一生?”一想到那个情景就觉得很可怕,就是你终其一生就是个二流、三流乃至四流的所谓文化人。因为那个时候我看过《傅雷家书》,傅雷觉得,从事文艺的话,一定要是一流的资质,一定要有一点天赋,所以他的儿子就去学钢琴。资质不好的,他觉得你就该老老实实去学一个可以致用的、而且不管高低是对这个社会有用的这样一个东西。当时这个话对我震动很大。
我就想那么怎么来判断我能不能做文学。之前文学只是一个爱好,但现在就面临一个选择,我要做还是不做。而且人到三十岁了,确实需要决定将来的发展方向。我焦虑这个。并不是我出了一本书,我很高兴,然后就去经营自己,根本就没有那样想过。
那么用什么方法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这个人跟这一片土地,跟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之间,有没有一个可以大家取得共振或者是感应的关系?如果没有,恐怕我的文学是走不到头的。如果是有,我就相信。所以我当时真的就是花了几个月时间在草原上漫游,而且全是徒步。后来我就觉得,我终于越走越踏实、越自信了,我觉得没有问题。
记者:可你之前不也在写这些吗?
阿来:之前只是作为爱好,不自觉地就开始做。因为我受的教育也很低,就不可能说我从小就有这么一个志向。而且刚开始做也是一个风尚使然,上个世纪80年代大家都在做,我们也确实没有事情。但做到这个程度你就必须想一想,你突然面临选择就是,你能不能成为最好的。当时我的想法就很简单,我能不能做最好,不能做最好就不做。我就踏踏实实去当个教书匠,那个时候我也确实在当地已经是很有名的,教书教得非常好。
记者:那通过这个漫游你确认的是什么呢?
阿来:就是我跟这块土地、跟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情感,而且大家互相之间确实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文学理论书上讲的那样一个概念。所以我诗歌里写:“三十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前行”,“我走上山冈,又走下山冈”。其实都很白,但是我相信今天读起来大家还是会感动。我还说“现在我看见,一个诗人诞生了”。那个是我自己宣布的。你现在看那个《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诗人帝王一般/巫师一般穿过草原/风是众多的嫔妃,有/流水的腰肢,小丘的胸脯”,我说草原,雷霆开放中央,四周是阳光的流苏飘拂,我就是那个巫师,我就是那个帝王。
记者:真好,30岁,你就可以把心放下了,从此这辈子你就知道自己的道路。那种感觉真让人羡慕。
阿来:啊,对。而且没有人分享,真的就是我一个人在草原上。
在我老去之前,我会把整个青藏高原再走一次,作为跟这个土地的告别
记者:那40岁那年的那一次漫游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又有《大地的阶梯》?
阿来:也是一种精神需要。《尘埃落定》用诗化的方式把这一片大地写过一遍之后,我觉得自己不能永远这样诗化下去,永远这样诗化地来理解这些东西。我要从一个真实的东西来还原。所以1999年才又参加云南出版社的“走进西藏”,才写《大地的阶梯》。为什么不用小说的方式写?就是觉得对我自己来讲,一定要把这片土地还原一次。
记者:《大地的阶梯》里,充满了让人感动和羡慕的瞬间,比如:“当我坐下来,采摘草莓,一颗颗扔进嘴里的时候,恍然又回到了牧羊的童年,放学后采摘野菜的童年。抬起头来,会望见某一座高山戴着冰雪的晶莹冠冕。我庆幸在我故乡的嘉绒土地上,还有着许多如此宽阔的人间净土,但是,对于我的双眼,对于我的双脚,对于我的内心来说,到达这些净土的荒凉的时间与空间都太长太长了。在这种时候,我不会阻止自己流出感激的泪水。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感谢命运让我如此轻易地就体会到了无边的幸福。我只感激命运让我不断看见。”像这种漫游,是不是有很多很多次?
阿来:很多次,年轻的时候。应该说阿坝那块地方,刨去一部分边远的,整个藏区怎么也有五六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我是一步步走过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文学给我的,一个是写作的过程,一个是漫游的过程,真的是无比奇妙。至于后来的很多东西,版税、得奖,当然也是高兴的事情,但是对于我自己的内心,其实谈不上什么触动。
相关链接:阿来:《空山》是《尘埃落定》后又一场恋爱
相关专题:
阿来作品:《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