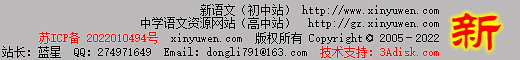金子无疑是一位有才华的自由撰稿人,她的作品里充满青春的躁动、成长的烦恼、游走的灵魂、女性的叛逆和玫瑰色的幻想。读她的小说,包括两部长篇《时间灰烬》和《玫瑰花精》,可以感到她的写作带有更多的自发性,活力灌注,叙述中流淌着生命的诉歌。
作为青春派的女作家,金子的女性意识是活跃的,喜欢处理有关女性成长的题材,《玫瑰花精》也是如此。实际上在现时代,年轻女性的成长是一个重要的选题,也许没有人统计过,在每年流入都市的年龄在18至28岁的女孩子中,有多大比例的人经历过憧憬、奋斗和幻灭。生存环境迅速消解了她们本来持守的信念,她们很快又化为环境的一部分去消解另一批人的意志。女性的自由和解放没有像今天这样彻底过,而生为第二性的压迫感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得到格外的凸现。
《玫瑰花精》中的一双姐妹,秧秧和笛子,都是有家庭庇护,学到了专业技能,无衣食之忧的女孩子,然而她们在都市里同样经历了刻骨铭心的蜕变。她们的经历有关爱情,而爱情正是教育女性觉醒和成长的主修课程。
这部书中的关键词也许关乎非理性的背叛,全书正是由一系列的背叛故事组成。先是出现了一个和睦家庭的分裂,父亲被女学生诱惑,背叛了母亲和两个女儿另组家庭;接着是秧秧背叛了家教,变得任性不羁;以后男友乔晋背叛了秧秧,转而追求笛子;再以后笛子背叛了姐姐,与乔晋产生私情;最后笛子背叛了自己,选择逃遁人生。这些背叛中只有笛子背叛自己是出于理性的复苏,其余背叛都具有非伦理性质,反映了所谓礼崩乐坏的伦理现实。
背叛对于情节是强有力的修辞手段,它引起了震动、惊讶和悬念,更何况所有背叛都发生在最亲近的人之间。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的倒下显然出于父亲的作用,父亲与母亲的婚姻原本牢不可破,两人共同奋斗多年,从边远地区迁移进大城市,进了艺术院校任教,可是忽然有一天,母亲在父亲眼中变得毫无魅力,视若陌路,只因父亲爱上了自己的女学生,女儿割腕也未能阻止他的决心。作品里,父亲在女儿眼里本是模范男人的表率,他的背叛自然带了原罪的意味,成为以下连锁反应的第一推动力。其实,父亲遇到的问题不是新问题,只是在过去年代,父亲是不敢如此果决的,即使畏葸于众人的口水也要掂量掂量,可是父亲赶上了好时候,他后来索性公开和钟爱的女学生在校园里走动了,这一壮举很快赢得了公众的同情,最后倒是母亲怯于舆论压力草率收场。这一过程复杂而惊心动魄,被金子描绘得有声有色。金子善写战争场面,两性间的战争,包括了夫妻、父女、恋人间的战争,每一次都出现有男性的背叛,她的写作表达了当代女性对男权话语的深深忧虑。
这不是一个老故事,是一个新故事。在故事中,男人和女人们缠绵着,对峙着,恩爱着,和互相提防着,策略上都比老情节有所改变,金子小说的一种新意就在于写出了男女间新的游戏规则。我们读到,书中涉及的新背景下,女性们对男性的态度有了很多退让,她们不再计较他们是否纯洁,和其他女人的关系如何,只在乎他们是否愿意和自己好下去,母亲对父亲的态度是这样,秧秧对乔晋、笛子对乔晋的态度也是这样。即便如此,她们还是不容易真正拢住男人的心。当然,作为代价,新时期的男人对女人也表现出宽容的姿态,乔晋明知道秧秧的过去,不作太多计较,可是,他对秧秧只是敷衍,敷衍是自我保护的高级形式,时间一到,谁也不能阻止他合情入理地抛弃秧秧,去寻找一个像笛子那样未经他人染指的女子。
反叛之风渐起,来自女性的背叛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秧秧之死就与妹妹有关。秧秧从来是笛子的保护神,到头来却未逃过背后插来的一刀。确实笛子是爱上乔晋的,她并无心伤害姐姐,不过这是一个新故事,在新故事中像她这样的女子会为自己想得更多一些,投入乔晋怀抱时顾虑更少一些,不大会念及姐姐的感受。笛子也在成长,她的成长是自我意识的逐步清醒和自我中心的逐步确立,就像父亲终以自我利益为最终取向那样,她对姐姐的背叛重演了母亲遭到背叛的一幕。《玫瑰花精》讲述的背叛故事,曲折地反映了我们现时期生活某方面的一种表征,非理性、感情泛滥和缺乏责任感,透视了集体伦理向自我伦理的转变。
金子在叙述上毫不困难,这得益于她生动的形象捕捉能力和想象力,以及对语言的感受。她是一个画家,擅长使用线条、比例和色块表达对世界的观感,同时也工于用文字堆砌起类似海市蜃楼的城堡。
《玫瑰花精》所发散的想象力是动人的。人们读了此书,很容易猜想它带有自述状性质,起码猜想作者有过一个反目的家庭,有一个姐姐或妹妹,因为书中大量体验性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似乎只能出自临摹,但其实谬矣,其实作者父母感情甚笃,本人也不曾有过一个姐妹相伴,只有个比她大了五岁多的哥哥。这样反过来看,就不能不对作者的想象能力大加称道了——并不是所有称为作家的人都具有这种出色的能力,有些人写得很精彩,但只能复述自己的经验。所以,金子可能是一个更适合写作的人。
凭空虚构出的人物和身边的人物,在金子的脑海里恐怕没有大的差别,从活跃的文体中可以看出,她对创造出来的人物兴味盎然,这是进入佳境的表现。小说中刻画最生动的应该是秧秧,她任性,敢作敢为,我行我素,内容因有了她而生机勃勃。这个秧秧从小给妹妹讲恐怖故事,常带着妹妹与各色人等交涉,打过父亲情妇一个耳光,约来男孩砸过楼上邻居的玻璃,带了妹妹去向父亲要过生活费。她的口头禅是“郁闷”和“崩溃”——正是这一代青年人的格言。这个秧秧又是妩媚和脆弱的,被父亲打了以后,哭着往往门外跑,却跑错方向上了楼梯;她在男友面前撒娇,不接他递来的烟却非要叼他嘴里那根;男友变了心,她又一下子变得惶惑,连做爱都再也拿不出过去的格调。金子塑造的秧秧是时尚的,也是没有前途的,是勇敢的,也是虚弱的,她的命运足以唤起众多青春女子的共鸣,因而也是典型的。
不仅对于秧秧,对于其他女性形象的塑造在金子来说也是长项,显得得心应手。实际上她对同性的观察和体味,与她们心灵上的沟通远比一般男性作家细微深入。她书中的女性都是眉眼鲜活的,笛子小时候坐在地板上哭,看见鞋上的兔子笑,会揪着兔子的耳朵,一点一点地揪;大姑娘了,在乔晋面前吃饭,心里有委屈,会夹了菜,放在自己碗里,用筷子一点一点的戳。由于有了这些细小的地方,不由得读者的感受不真切。那个父亲的情妇,大四的女生,见情人的孩子来找,态度原是倨傲的,可是当她被比她小的秧秧打了耳光后,她的反应不是暴怒,而是“当即就哭了起来,边哭边负气地一屁股坐在床上,然后突然甩着头歇斯底里地叫着:‘滚出去!’”——这种描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仔细想又尽在妙处,符合一个几乎少不更事的年轻情妇的心理神态,见出了作者的功力。金子写女性能够写出女人味,这女人味儿不是描摹来的,不是揣摩来的,而是随意点染成的。去比较一些号称善写女性的男作家,他们笔下的女性有时显得空洞——也许出于兴趣他们更善于渲染她们的美貌,但缺乏金子写成的韵味。
由此我们想到,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先天的,一种是后天的,先天的作家传神,后天的作家达意。
我想,金子属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