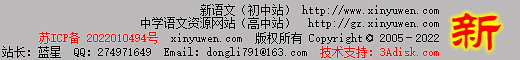因此,当读到徐晓的《半生为人》这部散文集时,我为之震惊。我曾经零星地读过徐晓的一些散文,感觉她始终生存在一段历史之中,和当下的语境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在许多人已经失去了凭吊历史的勇气和能力之后,徐晓仍然如此执著,不能不让我动容。尽管我并不完全认同徐晓的价值取向,甚至认为她如果稍微放松一点笔墨,她的文体可能更漂亮。但是,这些并不重要。徐晓的散文是久违了的一种文字,那种穿心而过的文字。她在对一代人的精神史的叙述、倾诉、透析和追问中,传递了生命的疼痛感。当她在张扬个体时,她并未将个体拔出脚下的大地。这使她的疼痛感扩大而成为一种始终和历史息息相关的精神震颤。所以,我在读这本书时,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心理张力。
徐晓对今天的散文写作充满了启示:散文的艺术问题与写作者的思想、精神、生命状况密切相关,它的成熟与发达总是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怀、胸襟和人格的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样思考问题,我们或许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作者一旦进入散文领域便捉襟见肘。散文实在是一种无法遮拦的文体,如果反其道而偏要去遮拦或者搪塞,那么势必和散文越走越远。现在的问题是,汉语的表达能力和技巧已经足以承担散文的功能,但在实际的写作中恰恰相反,过度的技巧和能力缓解了生命的疼痛和精神的紧张,作者在文体中消失了。
很多人都注意到我前两年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一些朋友曾经认为我所说的“文化大散文”的终结有些危言耸听。其实,我是比较早的维护这一文体的读者之一,但我仍然坚持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大散文的式微,恰恰是因为这种文体的逐渐膨胀转化为散文写作中的“文化决定论”。当学问、知识成为散文的叙述主体时,它可能丢失写作者的情怀、胸襟和人格以及知识叙述中的文化关怀,冷淡写作者的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散文的知识性论述和文化的考古,而是强调不应当放弃用自己的灵魂去穿透论述与考古背后的东西。另外一层意思是,知识或者文化的力量在散文中应当是学养的蕴藉和价值的取舍。许多人看中张中行的散文,应当与此有关。在当代散文史上,张中行的重要性无可争议,但我同时觉得他的意义被夸大了,也被误读了。我们不必老是用国学大师的名分来评判一个写作者,在放大的历史框架论述,张中行的学问虽然很大,但并无特别强调的必要。不必说今天,知识者的几代中,上世纪30年代的看20年代的,40年代的看30年代的,50年代的看40年代的,大概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这是教育背景的差异。张中行的重要与他是不是国学大师并无关系,而在于他的情怀,一种伤逝般的情怀。在他的笔下始终呈现的是在今天的语境中已经不复存在的一种文化传统和一代文人的心迹。他在追忆之中流淌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是张中行式的“疼痛”。这种难以再现和复制的情怀正在逐渐消失,反映了当下文化生态的某些征候。
闲云野鹤式的文字当然好,但名士有真假之分。即便如梁实秋写出了《雅舍小品》这样的文字,但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散文家之一。
我们的散文实在缺少大痛苦的东西。无病呻吟自然与我说的大痛苦没有关系。(王尧)
(编辑 小题)
新浪连载:
徐晓:半生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