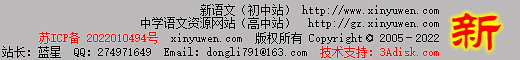战士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战斗的。现代战争越来越重视后勤工作,甚至有的军事专家认为,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对于一个思想战士来说,生活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战斗的情绪和战斗的结果。
鲁迅是个非常有生活情调、生活智慧的人。
他的人生观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后来又解释道:“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鲁迅很重视钱,绝不假装清高。有个书商骗了我和余杰、摩罗等人的钱,我们跟他交涉,他却对我们说:你们知识分子怎么这么庸俗、这么爱钱啊?你们是灵魂工作者啊!我不听他的欺哄,就学习鲁迅,一定要跟他算账。
鲁迅的日记里仔仔细细地记着他的几乎每一笔收入支出。他的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薪水、讲课费、稿费。后两者是不定的,所以他很看重固定的薪水。他在教育部每月可以拿300大洋。那时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两三块大洋。一块大洋购买基本生活品的购买力大约是今天一块人民币的七八十倍到一百倍。举个例子:根据老舍的回忆,当时老舍当个“劝学员”——教育分局局长,每月100元,小学校长40元,小学老师25元,学校的勤务员6元。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工性质的管理员8元,而馆长李大钊300元。老舍说当时1毛5就可以吃顿很好的饭:一份炒肉丝,三个火烧,一碗馄饨带两个鸡蛋,这些只要1毛二三,如果1毛5,就可以再来一壶老白干喝喝了。这一顿饭现在在北京,15元恐怕还未必能拿下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很看重他的300大洋。所以前边说的,他跟章士钊打官司,也有经济原因,一定要保住自己的铁饭碗——章士钊免了鲁迅的职,许多人等着谋他的缺呢。后来,他离开了官场,也离开了大学,由广东到上海。领导教育部的蔡元培先生每月给他干薪300大洋,他也接受了。有人不理解鲁迅的做法,说鲁迅为什么拿着国民党政府的钱,还要骂国民党。在鲁迅看来,钱是该拿的,但骂也是该骂的。跑到外国去,在帝国主义的大旗下面骂中国,那是没出息的表现。我就在国内以笔作枪,贬恶扬善,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真正的勇士,真正的豪杰。
鲁迅有个学生叫李秉中,在军队当官,想辞职不干了,写信征求鲁迅意见。鲁迅反对,认为饭碗可以跟理想分开。鲁迅回信说:“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鲁迅居然说出“混混”这样的话,很不英雄吧?很不容易理解吧?其实重视饭碗,重视物质生活对于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态度。鲁迅不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的这个真理,而是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得到的。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所以,我也不避讳“钱”字。到饭店吃饭,我一般不说什么“买单”那种文理不通的话,我就直接说:算钱。而且还要检查一下账单——当然,如果跟女朋友吃饭,就算了。
可见,鲁迅的生活智慧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上的。生活搞不好,仍然追求理想,当然也值得尊敬,我们应该帮助这样的“有志”青年。但是不要把二者绝然分开,一味追求理想,不顾生活实际,那就可能成为“幼稚”青年了。
他在生活中的智慧,使他在思想上、在文章里都明察秋毫。
所以,他知道如何应付不同的场面。比如他说如何听高人讲话:“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做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小杂感》)
这是世故,但这世故背后是对虚伪的社会风气的冷嘲。他也有直率的时候,比如日本请他主持中日通航典礼,他拒绝逢场作戏。他说:“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记者纠缠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答道:“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智慧不一定都是圆融婉转的,有时候也表现为斩钉截铁的果断。
鲁迅在《世故三味》中写道: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那么,鲁迅的世故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的世故呢?他的好友许寿棠说:“有人以为鲁迅长于世故,却又有人以为他不通世故,其实都不尽然,只是与时宜不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