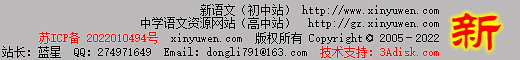原著 史铁生
改编 罗登
 | |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了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在它周围,而且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着中间有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年。
 | |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且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进入了这园子,就再没有长久的离开过它。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也找不到了,我就摇着轮椅总是到它那去,仅为着哪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 |
记不清都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 ,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就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所以,十五年来了,我还是总得到古园里去,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 |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会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母亲知道有些问题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悟出当我不在家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的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以她的聪慧与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黑夜后的白天……
而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加倍的 。——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的最苦的母亲。
在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走遍了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突然熬不住了? 我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对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
 | |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和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的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的走,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曾经好几回,我在园子里呆久了,母亲就来找我。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样子。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了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悔恨,丝毫也没有骄傲。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 |
若有一位园神,他一定注意到我了。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轻松快乐,有时沉郁苦闷,有时优哉游哉,有时彷徨寂寞,有时平静而自信,有时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来骚扰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吗要写作?
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会事,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
可我不怕死,有时候我真的不怕死。
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的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与福祉。
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个孩子,还是像个老人。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