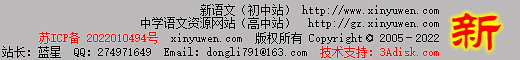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
李白是时代的骄子,一出现就震惊了整个诗坛。他气狭风雷的诗歌创作,及其天才大手笔,当时就征服了众多的读者,朝野上下,许为奇才,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李白是一位旷世奇才,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但是,人们在盛赞李白的“斗酒诗百篇”的创作豪情和“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盖世绝伦的神奇艺术感染力的同时,却不得不对这位顶礼膜拜的心中偶像的坎坷、悲愤的一生的慨叹与惋惜。按理说,盛唐孕育了天才诗人,诗人将唐诗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像这样一位旷世奇才,应该是宏图大展,平步青云,人生如意,功德名标青史而唾手可得。假如是这样一位罕见的诗人,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用一种政治的手段来推动文化的进步,那唐代文化的成就领域就绝非是仅限于唐诗;而且有着这种成就的人也决不会是廖若晨星。然而,李白的一生也许是与政治相背离的,所以充满了坎坷和艰辛。更可叹的是“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报负化为泡影。是他自己想作一位不问政治的闲云野鹤吗?不是的。是他自己想求仙访道,不问红尘,作一个与世无争的圣贤吗?更不是。他与一般盛唐士人一样,是一个功名心很强的诗人,但他又不愿意走科举入仕之路,想像古代的策士一样,“编干诸候”,“历抵卿相”,寄希望风云际会,一鸣惊人。与25岁就开始了长达18年的漫游与干谒生活,想实现自己的“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理想。干谒失败后,隐于徂徕山,到42岁,天宝元年(742)才奉召二入长安,他自以为时机以到,在《南京别儿童入京》诗中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好景如昙花一现,他终因其狂放的性格和行为触怒了朝中的权贵,遭到谗毁,于天宝三年以“赐金放还”之名,被迫离开长安。此后,李白寄家东鲁,开始了漂泊十年的第二次漫游。特别是他于暮年时期,在752年,误入永王李嶙的幕府,当永王以叛乱罪被肃宗李亨下令讨伐时,李白也以反叛罪,蒙冤入狱,并长流夜郎。759年,李白在流放的途中遇赦放回,他悲愤交加,次年病逝于当涂,年仅62岁。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败笔,使他遗恨终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位旷世奇才难展胸图大志,并且一生坎坷、漂流、悲愤、艰辛,以致含冤蒙羞地死去呢?翻开李白沉重的人生档案,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权贵们的嫉贤妒能外,更主要的是他自己那种狂傲不羁、自视清高、自以为是、喜为大言、目中无人、“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性格,造就了他悲惨的人生。也许人们会翘起大拇指称赞说,人生的悲剧美在李白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是又有谁愿意自己亲身实践着这种人生的悲剧美呢?
李白那种平交诸候,长揖万乘的人生理想过于高傲自负,过于理想化,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浪漫主义与严峻的现实矛盾,常使李白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可是他又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要漂流、漫游、流放和蒙羞。
然而,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有几多人,他们的才华远不及李白的百万份之一,与李白相比,可以说是胸无点墨;但是他们的狂傲之心与李白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自己“身现强虏尽,谈笑静胡沙”。我想,这种人是没有好结果的。它自己不学无术,却又要自高自大,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行,似乎天底下只有他才是对的,可就是没有人认可。所以,我奉劝一切有识之士,在拜读李白壮丽诗篇的同时,又要以李白的人生悲剧为借鉴,不能让李白的人生悲剧在你的身上重演。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时自省,处处谦虚,审时度势,左右逢源,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更臻完美,才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成为一个为社会所用的人。事实上,一切希望成功的人,处世为人的艺术尤为重要。一个不会处世,不会生存,不会做人的人,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人材,他的人生也一定不会很完美。即使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与政治家的雄才大略,放眼全球的胸怀与眼光相比,不知要渺小多少倍。你在政治家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介书生,文人、墨客而已。如果文人墨客就自以为了不起,也“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话,那他将会与人生悲剧共度一生。
愿天下有识之士,在效仿李白飘逸洒脱的气度和自信豁达的精神风貌的同时,摒弃那种自命不凡,喜为大言,孤傲不群,狂放不羁的性格。只有这样,你的人生才会与时俱进,充满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