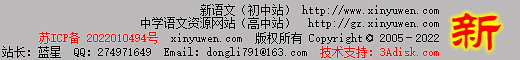屈原与陶渊明,代表了两种人生模式,或云载道文化与闲情文化之别。一般士人,往往既做不了屈原,又做不了陶渊明,只是跟着屈原愤世嫉俗,深恶痛绝地指责而不付诸行动,跟着陶渊明吟唱自赏而行动上另有所图或远离诗意。通过长期领悟屈原,揣摩陶潜,对话沟通,触类联想,我更多地从二者之异中看到了明显的“同”。出身与来历他们均为元世显赫,当代没落,屈原唯一可以炫耀的是“帝高阳之苗裔”,至于父、祖辈,似乎无可称道,诗云“忽忘身之贱贫”,“贱贫”可能反映了比较真实的情况。陶渊明虽有曾祖陶侃光环的映照,但“昭穆既远,已为路人”(《赠长沙公》),故“少而贫苦”。大起大落的家庭阴影,由盛转衰的严峻挑战,良好文化教育的熏陶,使他们成为政治上积极进取的文人。但是,少年时代的巨大打击,在心理气质上留下了久远的阴影。屈原“生于国而长于野”,其中显然包括家庭悲剧的“蛛丝马迹”,有人推测为“英雄弃儿”似嫌过份,但父辈没有留给他财产、业绩,则显然是事实。陶渊明八岁丧父,而且其父“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命子》),亦明其事业无成。可见家庭留给他们的是遥远的回忆,现实的困窘,良好的教育,情绪的起伏,情感的脆弱。屈原没有在作品中言及自己的儿子,我们只能如此推测:即使有儿辈,亦无所作为。根据屈原的心态与习惯,如果儿子有所作为,那一定要大书特书聊以慰藉的。陶渊明饮酒过度,导致五个儿子智商不高,雍、端二子13岁那年,还难于区分“六”与“七”,不是痴呆又是什么?一一这样理解,虽然有所偏颇,违背了陶潜“贬”子蕴爱的本旨,但五个儿子平庸无成,亦是事实。追溯二人家族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如一颗明亮的彗星,迅速升起,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只不过在广袤的天空中留下一道渐渐淡褪,又永恒难灭的痕迹;他们虽然来有影,去有踪,但无法寻代那源远流长,极为显赫的家庭背景,又找不到子孙绵延,事业家传的家庭线索。家庭的精华似乎正如代代蓄积的能量,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作了“一次性释放”,从而也就染上了一层伟大、神秘的色彩!才能与志向他们的志向主要在政治仕途方面,可谓远大、执着。屈原的志向正在辅君之“美政”,举贤授能,君臣契合,“循绳墨而不颇”,“及前王之踵武”。而陶渊明亦不同寻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论及实际的治国才能,则令人遗憾,屈大夫才气横溢,娴于辞令是事实,只是将繁杂的政治思想化、简单化,认为“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女矣”(《惜往日》)。他对自己才能的过高估计,导致了他的孤高自傲的高价值取向的形成。他缺乏从政入世的“苦难”准备,缺乏政治家宽阔的胸怀、胆略气魄,缺乏在社会关系中从容冷静、兼容协调的组织能力。屈原不能身居高位,是他的伤心处;假如真让他握有重权,推行改革,楚国也未必治得好。陶渊明做过祭酒、参军一类的小官,没有看出什么政绩与才能;他一方面很想做官,但官儿太小又不想好好干,所以刚刚到任,则又“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于是又隐居,因“家贫”与理想,则又出仕。十三年中,时仕时归,亦官亦隐,经过长久思考、选择,最后走上归隐之路。同样,在个性气质上,陶渊明亦不宜为官,他自己说:“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故要求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们对政治仕途的过高期望,对自身才能的过高估价,必然将“有志不获聘”的原因归结于政治黑暗,忠佞倒置,世风日下,无一可取。读读屈原的《离骚》《九章》,同时代哪里还能找到一个好人、一个贤臣,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且看《离骚》中所述:“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固时俗之工巧兮,亻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世并举而好朋兮”,“世溷浊而不分兮”,“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陶之归隐,他曾强调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质性自然”,但另一方面亦愤世嫉俗地归结为社会黑暗,无法生存,如“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饮酒》之六)、“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饮酒》之十二),故将出仕比为“误落尘网中”。他的《感士不遇赋》更是直接、愤激: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学,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所以他们的创作,很少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总是或远或近、或隐或现地与政治失落、怀才不遇有关。矛盾与斗争可以这样说,屈之沉湘,陶之隐逸,均是远大志向、政治理想与现实矛盾无法调和的结果。他们个性执着,与众不同,我行我素,常常令人不解,加之朋友有限,社会交流不广,以致给人们造成一种精神失常或心理病态的假象。其实,我们的诗人与一般的人一样,均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同样有做官的强烈欲望,更有“官本位”潜意识的痛苦的煎熬。他们在漫长的流放疏远之中,隐居躬耕之中,经受过无数次的犹豫、思考、彷徨、矛盾、斗争。他们的作品,正是他们心灵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是他们苦难历程的真实记录。他们的作品,准确地说,应是人生思索的“文学日记”或“日记题材的诗文”。无独有偶,屈原行吟泽畔,遇到了好心的渔父劝告;陶潜归隐弃官,遇到了好心的田父的劝告。且看他们的劝词:渔父田父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其氵屈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饣甫其糟而其酉丽?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再看他们的回答:屈原说:“安能以自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陶渊明说:“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之九)从二位诗人的作品来看,渔父、田父应该实有其人,而且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对其遭遇、处境是同情关心的,其劝告是发自肺腑的,其劝词亦是世俗的、普通的、随和的选择。二父所言,亦是二子思想斗争中不可回避的真实的一个方面。二子将其劝词写进作品,亦是承认在人生道路上确实还有自己抉择之外的选择,而且这一选择,也曾经对他们产生过动摇与影响。他们自身也曾有过这方面的考虑与斗争。只要看看二子的答词,无一例外地选择反问句式,即可见其一斑。反诘有力,表明自己的坚定执着,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因为对方击中自己的弱点,通过反诘来克服、克制、限制自身的弱点与动摇。这种反诘与其说是针对二父的,不如说是针对自身心灵深处的犹疑、动摇。通过反诘的强化以坚其志。由此观之,屈、陶之伟大,不在于表层上的选择与坚持:屈原被疏被放后决不屈服,沉湘以抗;陶渊明弃官归田之后决不出仕、终穷一生,而在于他们心理自我调节、自我平衡、自我净化、自我升华的胜利与成功。他们不掩饰自己的矛盾与动摇,他们能够正确地直接面对这种矛盾与动摇,从而通过自我调节与平衡,克服这种矛盾与动摇。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真实可信的心灵脉搏的跳动,有血有肉的苦难人生的追求,同于常人而又超于常人的可贵之处。假如我们对渔父、田父的解读,还感到不太可信的话,我们还可以找出众多的旁证。如《离骚》中的女须、灵氛、巫咸之词,《卜居》中的八种选择。选择代表了矛盾与动摇;选择,又显示了矛盾与斗争后的归趋与倾向。八问之中,如果说一、二问还多少带有可供选择的性质,那么,三至八问则明显为一是一非,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陶渊明自己就更坦率了,“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之五)。“贫”与“富”代表了两种选择:出仕?还是坚持隐居?两种思想在心里常常发生激烈的斗争,令人欣慰的是,最终“道义”战胜“出仕”。他的《饮酒》组诗亦常通过反问句式来表达他的矛盾、斗争,如“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之二)“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之十二)、“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之十五)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矛盾、动摇、斗争,他写下这些干什么呢?他的《归去来兮辞》向来获得好评,或称为辞官归隐的宣言书。窃以为此言过矣,此篇正是陶渊明冲动弃官、回家犹疑之后“以坚隐志”的作品。全篇采用了三种句式、三种时态。写现实思想矛盾,则采用充满理性的反诘句式,如“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这种反问本身,正是其归隐之后无法掩饰的追悔、动摇、矛盾心情的反应,亦是斗争以“道胜”为结局而以坚其志。写归田经过,则采用夸张、放大的手法,如云“草屋八九间”的住宅有“衡宇”、“园”、“松菊”等,同《归园田居》诗中“榆柳”、“桃李”、“深巷”、“户庭”一样,都是心灵化的描写,是所谓“无官一身轻”的自我安慰。写将来生活安排,则采用“或”字句式,写出绚丽浪漫的隐逸安排。这种超自然、超客观的描写与美化,也是其官本位失落之后的“异化”反映。寂寞与孤独伟人的心灵总是超越世俗的,其精神需求达到最高层次,其痛苦与忧愁,寂寞与孤独,也就达到最高程度,有人称之为“伟人宇宙孤独感”。用罗曼·罗兰的话来说,他们是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是远远走在现代文明之前的人,是被一般人误解、非议、“诬蔑”的人。陶渊明也是寂寞、孤独的伟大诗人,他的孤独首先呈现在作品中。屈原的孤独是没有人理解他,“众人皆醉吾独醒”,《惜诵》的抒发最有代表性:情沈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郁邑余亻宅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愿陈志而无路。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申亻宅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忄屯忄屯。而他的对立面又是如此的强大、众多,有“党人”、“众女”、“时俗”、“举世”、“众人”、“众谗人”。渊明隐居以后,也常常感到孤云无依、知音不存。其《饮酒》“序”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在《连雨独饮》中说:“自我抱兹独,亻黾亻免四十年”,时间实在太长了,常常“慷慨独悲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其《饮酒》结句云:“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被人斥为谬误,只好装醉汉,而无法将真实的心态表露出来,简直有阮籍《咏怀》味道,“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人间难觅知音,无法倾吐,只希望成为一只鸟,到千里之高空哀鸣倾诉!与屈原一样,渊明感到孤独,同时受到各方非议,如“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咏贫士》之二)、“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饮酒》之六)。渊明在《祭从弟敬远文》中,感激敬远对他隐居的理解:“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被众议。”而这一“唯一”的知音,亦于31岁那年过早去世了。颜延之很敬服渊明的不顾众议,“岂若夫子,因心违事。畏荣好古,薄身厚志。”(《陶征士诔》)因为孤独、没人理解,他们均将思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古贤前修中寻找知音。如屈原作品并没有直接点到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吴起、商鞅等。他涉及的“臣子”类人物分为两组:一是羡慕的前贤,如挚、咎繇、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可谓“得志”组)。二是自慰的前修,如伯夷、比千、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可谓“失意”殉节组)。屈原正是从他们身上借以自慰,汲取力量。渊明隐居后,受到“众议”,故亦大量引古贤古隐为“知音”,如“羲皇上人”,逝然不顾,被褐幽居”的鲁二儒、“采薇高歌,慨想黄虞”的夷齐、“去矣寻名山,上山岂知反”的尚长与禽庆、荷艹条丈人、长沮桀溺、於陵仲子、张长公、丙曼容、郑次都、薛孟尝、邵平、荣启期、黄绮、黔娄、黄子廉、疏广、疏受,并且自称“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屈陶二子的“寂寞与孤独”,是他们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屈子的敏感多愁憔悴失意、过份的耿直、过份的执着,加之几分狂态,几分醉意,几分痴迷,几分迂阔,使他与同时代的人造成了巨大的隔膜,几乎没有给予一点点与其历史价值相称的关注,使得当时的历史、文化著作对他没有作出片言只字的记载。即使跟别的狂人、隐士相比,屈原也最不引人注目,所以连名字也没有被点一点。他的诗歌,是其始所未及的政治上失败的结果,那些泄愤、容情的大量诗作“日记体诗”,他自己根本没有认识到那种伟大的传播价值,自然人们没法了解他,进而就认为“不需”、“不值得”了解他,乃至于他的生年、卒年、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妻子儿女、流放次数,使得我们无从得知。了解他的生卒年,我们只有两个依据,一是《离骚》的两句诗:“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二是楚怀王、楚顷襄王的生卒、任期。但推论出的结果大相径庭,林庚以为41岁,蒋天枢以为78岁,相距甚远。陶渊明的遭遇亦是如此,他的生活面不广,官位较低,长期隐居不仕,大家公认为“隐士”。他的诗歌亦是不公开传播的“日记体诗”,是安贫守拙的自慰,孤独苦闷的释放,尘世哀怨的解脱,苦难历程的记录。如《有会而作》“序”云:旧谷即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才)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此诗写自己隐居生活的艰难,写自己的思想矛盾与斗争:是丧志而食“嗟来”,还是学古贤而固穷?最后肯定后者:“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而“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正是此诗写作目的,将自己从苦难磨炼出来的感悟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以勉励自己的儿孙。由此可见,他作诗是不求闻达于当时,只是为了传之于后人,让自己的儿孙们通过诗作了解自己“为什么与众不同,坚持隐居”这种隐士生涯的副产品,由于主观的制约而没有在当时诗坛产生任何影响。似乎连渊明最要好的朋友颜延之当时的诗坛领袖,也不知道渊明在写诗、能写诗、写出不朽的作品,故在其《陶征士诔》文中重点介绍“隐逸”个性、生活,至于文学成就,仅“文取指达”一句带过,表现出颜氏对渊明的宽容,因其隐逸高节而不对其文学创作过高要求。这样,刘勰《文心雕龙》、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以及晋宋各史传均不论及陶诗,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钟嵘列入《诗品》,又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显然是将其诗歌作为隐逸高节的副产品看待的。至于屈、陶二人后来被评为“大诗人”、“中国十大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并以二人作品成为两门专学(屈学、陶学),则是他们没有料及的热烈与繁荣。理想与死亡AlbertCamus说:“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自杀问题,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①屈原、陶渊明浓厚的“死亡”意识、生死反思,也是深挚感人的。李泽厚认为,“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为‘惊彩绝艳’的头号主题”。②屈原感受到理想实现的无望、现实中无法生存的矛盾,如“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因而冷静、理智、悲愤地选择了死:“宁溘死以流亡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惟极于死以为态,故可任性孤行。”才敢于放言无惮,倾诉苦衷,问天咒地,评击谗佞,以“死”的代价给予现实全面否定,亦流露出对理想无法实现的眷恋。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影响于后代知识分子的,并不是其自杀行为本身,而是对死亡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是对死亡的冷静选择与思考。奥地利作家让·阿梅里认为:“自杀是荒诞的,但并不愚蠢,因为它以自己的荒诞不再加剧生命的荒诞,相反却减少了生命的荒诞。”③陶渊明对死亡的思考、处置就是平静而深沉的,求实而豁达的,“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所以他平静地写《拟挽歌辞三首》、《自祭文》、《与子俨等疏》,同样描写了现实社会的黑暗、自己事业的无成、发自内心的怨愤,如《与子俨等疏》云:“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自祭文》云:“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已荣,涅岂吾缁?扌卒兀穷庐,酣饮赋诗。”临死之前,对迫不得已的“弃官”,对导致自己弃官隐居的原因、对社会现实的压抑氛围,仍然是耿耿于怀,满含愤慨,不能自己;官本位潜意识的深层煎熬,仍然是深沉而强烈的。但又是躁动的、悲愤的、留恋而不甘的,这种深层的愤慨与眷恋,则与屈原的死亡意识相吻合。谈及陶渊明的思想渊源,人们更倾向于儒、道二家,而以道家为著。因为陶诗用“庄子”49次,用《论语》37次,用《列子》21次。李泽厚虽然认为陶渊明体现了儒道的融合但又偏于道,但亦认为陶渊明受到了屈原的影响,陶渊明的存在,是儒、道、屈合流的时代氛围影响的结果。④其实,陶潜受到屈原的影响、熏陶是明显的,他的《读史述九章》就专门写到《屈贾》: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服鸟献辞。诗云“如彼稷契”之忧,“逢世多疑”之忧,可谓“异代知音”。吴淞《论陶》云:“出处用舍之道,无限低徊感慨,悉以自况,非漫然咏史者。”此外,《读山海经》之十二亦咏到屈原之不幸:“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将屈原被放,归之于“怀王之迷”,亦是明智、深刻的史识与见地。渊明的《感士不遇赋》抨击世风溷浊,“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闾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其例证之一就是:“三闾发‘已矣’之哀”!此用《离骚》“乱辞”之典:“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鉴此,陶渊明用屈、咏屈的次数虽然不多,其理解、寄托却极深。文学艺术传播的线索,往往不是通过数量统计来确定的。陶渊明受到的影响与熏陶是多方面的,儒道兼收而偏于儒的屈原、以孔子为主的儒家、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屈兼融而偏于屈的阮籍,等等。而就美学传统而言,对陶渊明的影响,道家是主体,儒家是深层的,屈原是潜在的;道家是诗歌的,儒家的哲学的,屈原是精神的。
①AlbertCamua,Themythofaiagphua
②④见李泽厚《华夏美学》
③让·阿梅里《自杀·论自杀》,斯图加特克莱特考塔出版社,1983年出版
荆州师专学报 97 (06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