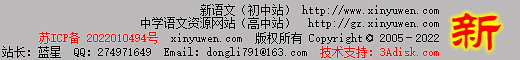我自己刚刚出了一本《非常道》,当阳泉把《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给我的时候,我觉得两本书有相通之处。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东西,我想和阳泉一样,我们虽然看到了那么多有意义或者非常宏大的叙事,但最终我们所关注的还是一些细节的东西。我小时候就对人们的谈话非常感兴趣,我发觉话语本身是有生命的,有力量的,有是非对错的,甚至有品相的。到大学接触中国的文史更多,更觉得中国人说的话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特别有意思。我读《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时,就发现第一部中“令人费解的童谣”和我以前听中国人说话是一样的,特别的低幼,非常有意思。
第二个就是我们对知识界自我的反思,有位文学界前辈曾经谈到,为什么你们写东西只能给自己看或者给圈内的朋友看,而不能做到1949年以前那些老辈学者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写出那些举重若轻的文字。后来想想,其实这种公共的表达方式还是可以努力的。有人将我的《非常道》和这本《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定位成《世说新语》一个类型,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肯定不是一路,因为它不是文人作品,不是主观性的作品,而是想为公共领域做一些示范和建设性的作品。用我的话来说,它就是一种历史写作,是用人性的眼光来打量我们的历史,并把它叙述下来。当读者读到这段历史时,不管是沉痛还是有趣,每个读者都可以自己选择当下的存在方式,知道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