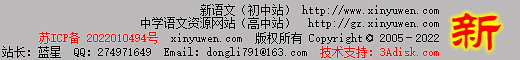每年3月青黄不接时,嫩绿的荠菜生出,母亲定要为我们采挖一些,贴补不足。荠菜的叶呈羽状分开,叶片上有齿形的缺刻,长出的花像白色的点子。
我家搬到湘子庙街后,隔一条马路,就是南城墙。记得在清明前,我也去城墙上和城河沿的环城林,帮母亲挖荠菜。提一只篮子,拿上一把小铲,在渐渐温润的风和刚刚醒来的树林寻找。有时候,还能采摘些野蘑菇。灰条和艾草此时还是干枯的,只在接近虚土的地方,才显露出一些湿气,让人觉得,生命仍然在其间存活着。
整整一个冬天,城墙和环城林绝少有人涉足。三九天河面也被冰封住,在上面向远处扔一块城砖,滑得比想象中的还要远。植物在渐次积厚的雪被下熟睡了一个冬天,大约到了惊蛰以后,潜伏起来不食的毛虫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了。荠菜比其他植物对春天的感受更灵敏,拨开一丛枯槁,它们已经在虚土上起身了。
通常阳面的荠菜长得肥壮,用手可以把它们连根拔起,细长的根须沾满零散的碎土末,贴近鼻子闻,有泥土特殊的香甜味儿。阴坡面的荠菜多趴在地面上长,颜色更绿一些,叶片瘦而长,若是清早或黄昏时起满一筐,它们每一棵叶面上都还蒙着一层灰白的雾霜,嘴里含上这样的叶瓣,除了荠菜本身的味道之外,那些霜尘慢慢化开的情形,似乎也能明确感觉到。
要是这时候来一场春雨,荠菜会长得更加嫩绿,城墙和环城林里,也会平添些生机。沿着河岸往林子的深处走,幽幽的地气,不断朝上蹿腾,林子里的气息此时也有所不同。土地和树木,一年里似乎只在这时候,才将独自拥有的那种鲜活的味道散发出来。它们在空中飘动着,散漫在林子和河面上,丝丝的气息渗透到我的神经里,让我还能感觉到身体里那些沉睡和潜藏的东西,正在被慢慢唤醒。被冻皲裂的双手,此时,也恢复起弹性,变得红润起来。一旦等到天热,所有的一切便逃得无影无踪,荠菜也会开出白色的花粒,星星点点,没有香气。
母亲通常把荠菜洗净,放进清水中再浸泡一阵子,然后,捞出置于面盆中,撒上面粉,掺和一些苞谷面,用一只手拌匀,放在蒸笼里,15分钟后便做成了荠菜麦饭。我和姐姐将蒜皮剥去,捣碎,母亲在蒜末表层撒一些盐,添上辣椒面,将一勺烧热的油泼上,调在碗中的麦饭里,这样,往往能吃出一头汗来。有时母亲也在上面浇一些红烧肉的汤汁,放上几块肥瘦相间的大肉块,吃起来肉的味道过浓,不及素吃着清淡。
荠菜在热锅里过水后,晾干水分,直接放在嘴里咀嚼,有少许的腥涩味,剩在锅里的汤,是清绿色的,喝了能解毒生津。我们家做凉拌荠菜时,母亲只在其中放少许盐,滴几滴香油,调些许陈醋。这是荠菜最正宗的做法,保持着原汁原味,汤水往往也被我大哥吃得干干净净。
清明前吃一顿荠菜饺子,是我过了旧历年后就一直热切盼望的。想一想荠菜拌上老豆腐,放上炒熟剁碎的鸡蛋,实在是件大美的事儿。我为此常跑到城墙和环城林里看荠菜起身了没有,然后把所见的情况告诉母亲。母亲会提早备好所需要的面粉,再去北院门老马家杂货铺子,购回上好的辣椒和调料,只待荠菜芽子冒出来,我们就最先尝到了新鲜。这一年余下的日子里,我便再没有什么牵挂了。
荠菜生出来的时候,多数菜店的货架上,由于节气的原因,往往是空荡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菜店当时不卖这种菜。前几年,一位朋友送我一袋子生在大棚里的荠菜,样子比野生的入眼。据说如今的超市里,摆放上了大棚荠菜,西安众多馆子里的荠菜饺子,就是由郊外的大棚,源源不断地供给着。
荠菜在我看来已属旧菜,也多年未见。想起来,会自然联系到从前的生活。对于我家来讲,它还是一种救急的菜,缺了,我们的汤锅里就连绿影都看不见了。在城墙上和环城林里挖荠菜,也像是我们随后的人生经历,尽管简单平凡,但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一种温润的气息。
(孙静杰摘自《美文》2006年5月上半月刊)
青年文摘网 www.21rea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