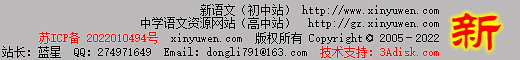三毛、王洛宾、贾平凹...写入20世纪末中国文化记忆的三个名字,他/她们有着共同的西部情结。谁能明了,三毛为何要在敦煌洒泪,为何一定要魂归敦煌...
 |
| 那个逝去的时代,有多少人为三毛扼腕叹息 |
1990年4月,还是那个烟雨迷蒙的春季,三毛第二次回到了祖国大陆。与她的首次大陆行,时间整整相距1年。与第1次轰轰烈烈相反,这一次她匿迹潜行,尽量回避记者。她先是到了北京,参加了由她编剧的《滚滚红尘》的拍摄工作,然后随摄制组赴东北拍外景。在北京,她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她去过王府井、西单,她还爬上了万里长城……她告别了摄制组,掉头去了祖国的大西北。她的行程大致如下:北京--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四川。西北的大雁塔、秦始皇兵马俑、敦煌莫高窟、戈壁沙漠、成都街头巷尾等都留下了她的足迹,都洒下过她的泪水。她本来要去拜访贾平凹,但是没有去。海峡两岸两位著名的文学家失之交臂。三毛最神往的地方,是敦煌莫高窟。
在去敦煌的路上,三毛百感交集--
大西北苍苍茫茫,天高地宽,唤起了她往昔在撒哈拉大沙漠时期的情感。
一股浓浓的乡愁。
她开始了另一种爱情--对于大西北裸露的土地,那片没有花朵的莽莽荒原的挚爱。
……
她把东西全部丢在车子的座位上,像听到了生命的召唤,不由自主地向没有绿意的荒原跑- -狂奔过去。
荒漠的一望无际的西北高原上,吹着坦坦荡荡的野风,卷裹着三毛那略显单薄的身体……三毛一阵阵惊喜。
在《夜半逾城--敦煌记》中,她忘情地写道:
在接近零度的空气里,生命又开始了它的悸动,灵魂苏醒的滋味,接近喜极而泣,又想尖叫起来。
很多年了,自从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不再感觉自己是一个大地的孩子,苍天的子民。很多人对我说:"心嘛,住在挤挤的台北市,心宽就好了呀。"我说:"没有这种功力,对不起。"
三毛站在万里长城的城墙上,别人都在兴致勃勃地看墙--古老斑驳、甚至有些残损的墙,她却仰头望天,自言自语道:
"天地宽宽大大,厚厚实实地将我接纳……"
一阵荒原的朔风,强劲地吹了过来。三毛觉得很惬意,她说:
"很快乐……吹掉了心中所有的捆绑。"
在去敦煌路上,三毛认识了一个同车的在莫高窟工作的旅伴,一个名字叫"伟文"的年轻人。这位叫"伟文"的年轻人,长年在莫高窟临摹壁画,他不仅是三毛的热情读者,三毛还觉得她与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缘。
在敦煌夜晚人影稀少的街头,三毛与伟文完全沉默地在大街小巷走着。三毛写道:
……风,在这个无声的城市里流浪。夜是如此的荒凉,我好似正被刀片轻轻割着,一刀一刀带些微疼地划过心头,我知道这开始了另一种爱情--对于大西北的土地;这片没有花朵的荒原。
在去敦煌的一路之上,三毛并不很在意车子经过了什么地方又到了什么地方。但有一个地方最让她心动,甚至一夜都"没有阖过眼"。三毛写道:
……只是在兰州飘雪的深夜里看到黄河的时候,心里喊了她一声"母亲"。
三毛希望能在莫高窟的一个洞穴里,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呆上一会儿,那个叫"伟文"的年轻人,帮她实现了这个愿望。
在《夜半逾城--敦煌记》中,三毛真真切切地写道:
在我们往敦煌市东南方鸣沙山东面断崖上的莫高窟开去时,我悄悄对伟文说:"你得帮我了,伟文,你是敦煌研究所的人。待会儿,我要一个人进洞子,我要安安静静地留在洞子里,并不敢指定要哪几个窟。我只求你把我跟参观的人隔开,我没有功力混在人群里面对壁画和彩塑,还没有完全走到这一步。求求你了--。"
"今天,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又说。
当那莫高窟连绵的洞穴出现在车窗玻璃上时,一阵眼热,哭了。
我打开了手电棒,昏黄的光圈下,出现了环绕七佛的飞天、舞乐、天龙八部、胁待眷属。我看到画中灯火辉煌、歌舞翩跹、繁华升平、管弦丝竹、宝池荡漾--。壁画开始流转起来,视线里出现了另一组好比幻灯片打在墙上的交叠画面--一个穿着绿色学生制服的女孩正坐在床沿自杀,她左腕和睡袍上的鲜血叠到壁画上的人身上去--那个少女一直长大一直长大并没有死。她的一生电影一般在墙上流过,紧紧交缠在画中那个繁花似锦的世界中,最后它们流到我身上来,满布了我白色的外套。
我吓得熄了光。
"我没有病。"我对自己说,"心理学的书上讲过:人,碰到极大冲击的时候,很自然地会把自己的一生,从头算起--。在这世界上,当我面对这巨大而神秘--属于我的生命密码时,这种强烈反应是自然的。"
我匍匐在弥勒菩萨巨大的塑像前,对菩萨说:"敦煌百姓在古老的传说和信仰里认为,只有住在兜率天宫里的你--'下生人间',天下才能太平。是不是?"
我仰望菩萨的面容,用不着手电筒了,菩萨脸上大放光明,眼神无比慈爱,我感应到菩萨将左手移到我的头上来轻轻抚过。
菩萨微笑,问:"你哭什么?"
我说:"苦海无边。"
菩萨又说:"你悟了吗?"
我不能回答,一时间热泪狂流出来。
我在弥勒菩萨的脚下哀哀痛哭不肯起身。
又听见说:"不肯走,就来吧。"
我说:"好。"
这时候,心里的尘埃被冲洗得干干净净,我跪在光光亮亮的洞里,再没有了激动的情绪。多久的时间过去了,我不知道。
"请菩萨安排,感动研究所,让我留下来做一个扫洞子的人。"我说。
菩萨叹了口气:"不在这里。你去人群里再过过,不要拒绝他们。放心放心,再有你回来的时候。"
我又坐了一会儿。
菩萨说:"来了就好。现在去吧。"
三毛从洞里走出来,有一种勘破红尘,参透人生的感觉。洞中菩萨大放光明的面容,无边慈爱的眼神,以及菩萨的微笑,菩萨的声音……三毛都久久不能忘怀。
黄昏了。
夕阳染红了远方那无边无际的沙漠。
三毛和伟文在离莫高窟不远的大泉河畔的白杨树林里散步--慢慢地走。他们谁也不说话,只是慢慢地走--向一片黄土高地一步一步地走去。
三毛看到了,夕阳照着土坡上三个坐着的身穿蓝衣的老婆婆。渐渐走近了,三毛听到了,她们口中吟唱着--反复吟唱着平常的调子:"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残阳如血。
在夕阳晚照中,三毛一脸庄重,神情肃穆,对站在她身边的伟文说,她死后想葬在这里:
"要是有那么一天,我活着不能回来,灰也是要回来的。伟文,记住了,这也是我埋骨的地方,那时候你得帮帮忙。"
伟文答应了她:
"不管你怎么回来,我都一样等你。"
在三毛与伟文约定以后不到一年,三毛又"回"到了莫高窟--她对伟文说的那个地方。三毛是怎样"回"到莫高窟的,贾平凹于1991年6月1日写的《佛事》中,有详细的记载。
贾平凹在病中写道:
5月29日天下大雨,有客从台湾来,自称姓陈,是三毛的朋友。一听说三毛,陌生客顿做亲近人;先生却立在那里只是说,我送三毛的遗物到敦煌去,经过西安一定要来看看你。
看看我?我望着先生,眼睛便有些涩了。先生既然是三毛的朋友,带了三毛的遗物去敦煌,冥冥之中,三毛的幽灵一定也是到了;我与先生素不相识,也无书信联系,这么大的雨,他从我的单位打问到我住的医院,偏偏我又从医院回来,他又冒雨寻来了。如此耐烦辛苦,活该是三毛的神使鬼差呢。
三毛,三毛,我轻声地叫起来了,"快让我瞧瞧!"等不及先生把一包东西放在桌上,我说,我要见三毛。
先生从一个大塑料包里往外掏,掏出一顶太阳帽来,说这是三毛生前一直戴着的;掏出一条发带,红色的,极有弹性;再是掏出一件水手裙了。先生的声调沉下来,介绍这种裙子在台湾一般有些年纪的妇女是不大敢穿的,四十多岁的人了,敢穿的恐怕只有三毛了。三毛天性坦真,最不愿约束。报上发表的一张照片,是她在成都的街头,赤了脚坐在一家木板门面前,样子顽皮如小狗。三毛穿了这件水手裙走着,走着的是个性,走着的是潇洒。先生还在掏着,是一件棉织衫,一条棉织裤,全是白色的,上边似乎还残留着几点什么斑痕。"我没有带她的袜子,"先生说,三毛是以长筒丝袜悬颈的,袜子对于我们都太刺激了。最后掏出来的是一色三毛十多年来一直喜欢用的西班牙产的餐纸,一瓶在沙漠上护肤的香水,一包美国香烟,淡味型的,硬纸盒里仅剩五支,明显地已经霉了。
从头到脚的穿戴,吃的用的小品,完整的一个三毛,出现在面前了。我久久地目视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能说什么呢,物在人去,生命已不可复得。
我走向了窗前,推开窗扇,檐前垂下的扯也扯不断那样的粗而白的雨。我喃喃起来,我并不自觉我说了些什么,是一句三毛你好,是一句阿弥陀佛?在场的我的妻子给我倒了一杯水,说我的脸色很是可怕了。
元月16日的清晨,三毛将最后的一封信,于亡日后第12天寄给了我,信上写着5月份她是要来西安的。那时候,看过信的人都感到遗憾,三毛果然不失言,她真的在5月的最后的日子来到了!我虽然见到的不是她的真人,但以她的性格,和我的性格,这种心灵的交流,是最好的会见方式。
先生说,他居住的地方与三毛家很近。他常常去她那儿聊天,三毛在生前曾对他说过,死后她希望一半葬在台北,一半就留到浙江乡下的油菜田边,但至她去年10月到过了西北,主意改变,希望能葬在敦煌前的鸣沙山上,她说她把地点方位都选好了。
鸣沙山,三毛真会为她选地方。那里我是去过的,多么神奇的山,全然净沙堆成,千人万人旅游登临,白天里山是矮小了,夜里四面的风又将山吹高吹大。那沙的流动呈一层薄雾,美丽如佛的灵光,且五音齐鸣,仙乐动听。更是那山的脚下,有清澄幽静月牙湖,没源头,也没水口,千万年来日不能晒干,风也吹不走,相传在那里出过天马。鸣沙山,月牙湖,连同莫高窟构成了艺术最奇艳的风光。三毛要把自己的一半永远安住在那里,她懂得美的,她懂得佛。
一生跑遍了世界,最后觉得最依恋的还是祖国的西北。鸣沙山可以重温到撒哈拉的故事,月牙湖可以浸润温柔的夜,喜欢音乐和绘画正好宜于在莫高窟。谁的一生活得如此美丽,死后又能选中这般地方浪漫?她是中国的作家,她的作品激动过海峡两岸无数的读者,她终于将自己的魂灵一半留在有日月潭的台北,一半遗给有月牙湖的西北。月亮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清纯之光照着一个美丽的灵魂。美丽的灵魂使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的读者永远记着了一个叫三毛的作家。
陈先生打开了厚厚的三本相册,都是三毛生前的照片,有一张拍摄的是三毛的灵堂,一张是三毛周日的场面:先生几乎是噙着泪水详细给我讲了三毛最后走了的事情。他说,在三毛死后,她的母亲在医院整理遗物,发现病床枕边还放着我的一本书。老太太感谢为三毛住院和后事帮了大忙的一位医生。那本书就送作纪念了。但是,陈先生却也带来了他送我的一件礼物,这就是三毛最后赠送给他的著作《滚滚红尘》:"我再送给你吧!"陈先生说,我浑身都在颤抖了,这何尝不又是三毛冥中的旨意呢?永久的纪念品,够我一生来珍存了。
我询问陈先生去敦煌以后怎样活动。陈先生说原准备到了鸣沙山,就在三毛选中的方位处修个衣冠冢,树一块碑子,但后来又想,立碑子太惊动地方,势必以后又会成为个旅游点,这不符合三毛的性格。她是真情诚实的人,不喜欢一切的虚张,所以就想在那里焚化遗物,这样更能安妥她的灵魂的。
这想法是对的,三毛还需要一块什么碑子吗?月牙湖的月亮就是她的碑子,鸣沙山就是她的碑子,她来来往往永驻于读者的心里,长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人世间有如此的大美,这就够了。 我深深地感谢着三毛的这位朋友,却遗憾我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同陈先生一块去敦煌。我送陈先生到大门口,在满天雨水的淋打中祝他一路顺利到敦煌。陈先生和我握别,脸上突然闪动了一个微笑。我立即觉得这微笑应该是三毛的,三毛式的微笑,她微笑着告别了。雨哗哗地下着,满地都是水泡,陈先生的身影消失在窄窄的长长的小巷的那头。这时候,灰蒙蒙的天上有了声音,是隐隐的雷,我知道三毛的灵魂在启行了,脱离了躯体的灵魂是更自由的。它在台北,它在敦煌,它随着月亮的周返转生两地,它会是做了月里的嫦娥,仙人之眼夜夜注视着她的祖国。它又会是在那莫高窟里做一个佛的,一个不生不死无生无死的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