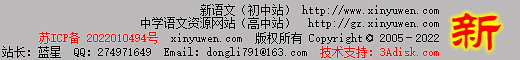古镇旧事
——回忆我的故乡岚河口
我的出生地岚河口,又名石泉坝、石泉铺。“石泉”这两个字来源于玉岚公社清泉四队的一口水井,在山脚下的一条沟里,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的先民,在青石沟里开凿了一口四四方方的水井,井边还有两方平整的井台,用来放水桶。由于年代久远,到了我们小时侯,有一块井台已经消磨大半,不那么平整了。据说在古代,石泉县的县城就在我们这里,是真是假,小孩子自然无法考证。岚河口属于汉江谷地,岚河在此汇入汉江,两条河流携带着泥沙,在此处遇上汉江流向大回转,水流变缓,形成了冲击小平原(我们当地叫“坝地”)。解放初期,坝地有800亩,到了七十年代末,经过重新丈量,已经有1200亩了。这坝地由河北、清泉、兴隆三个大队划分,这坝地既是我们的骄傲,也在每年夏天令我们揪心——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汉江边的坝地是肥沃的,土质松软,极易耕作,而且是夜潮土,不怕干旱,年出小麦、玉米、油菜三料,产量很高,是我们饭碗的希望所在。但是十年十涝(这涝主要危害的是玉米,小麦油菜是保收的),涝有小大之分,大涝漂江大水,一扫而光,颗粒无收;小涝淹没靠近河边的地方,还有几成的收成。屋后的山地丰富多彩,出产水稻、红薯、小杂粮,但是,收入也不稳定,十年九旱;粮食歉收,是那个年代的常事。吃饭不论在哪个年代都是头等大事,偏偏这个头等大事却不幸总是和一个“荒”结了缘,所以,我的这点回忆里,很多故事都是为了解决吃喝问题的。不象今天的人,平静而悠闲,不会为吃饭问题而担心。
正在消失的语言
安康方言,来自关中,经过长期演化,却又不尽相同。我当然不会在这里谈什么方言,而是回忆在那个饥饿年代里产生的,而今正在从人们口头消失的语言,或许能勾起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一点辛酸而美好的记忆,并且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世界并不是本来就是今天这个样子,今天这个丰衣足食局面是值得珍惜的,如果我们不珍惜、不努力,世界还可能回到原来那个样子。
“二三月”,这个词在那个年代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是荒月的意思。以现在的眼光,农历二三月,正是春暖花开,欣欣向荣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而在那个年月,农民的二三月是最难过的——年过完了,再苦的日子,年总是要奢侈一下的,接下来的日子就靠救济或者自救了。
“ 刨青”,要自救,除了借粮只有刨青了,因为谁家的日子都不宽余,借无可借。所谓刨青就是把正在生长子粒尚未饱满的庄稼收割了来吃。这还有一个辛酸的故事:旧时有爷孙两个,因为饥荒,在三月底去卖地买粮食,可是好话说尽,财主怎么也不肯买。想到地里的麦子已经有六成饱满了,爷爷说:“孙娃子,走,回去刨青!”
“一烧、二擀、三拌汤”这个短语,不解释,很多人是不理解的。这是说面食的吃法的,而且意思重在强调节约,而不是强调什么最好吃。一烧指火烧馍,好吃,但最浪费;二擀指擀面,好吃和浪费都是第二名;酸菜拌汤,最节省,是日常食品。
“ 炒七不炒八,九里炒莲花”,七八九指的是腊月二十七至二十九这三天,炒是炒包谷花、红苕爿、天星米等物,是过年的吃货(零食),平日是没有的。至于为什么炒七不炒八,我至今不明白(九里炒莲花的意思是说这一天炒的包谷花炸的花格外好,象莲花一样.我当时就认为不一定,二十九炒的也出死米子,不开花)。猜想是在贫穷的年代,为了节省而定的规矩吧,但是也不象,因为七比八还早一天。这个习俗对现在的小孩已经无所谓了,好吃的东西多的是,但是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却是非常盼望的。一般在二十七之前,我们就在岚河汉江交汇处的下方去揽粗沙,十几里的沙坝,只有这里的粗沙最好,黑颜色,而且是铁质的,我们用吸铁石试过。粗沙炒货熟的均匀而且不沾染食物,细发的人家会用几年。
“ 起旱”,是步行的意思。那时,公路交通还很不发达,水运却很红火,可上达汉中下通汉口。汉江河里木船、机动船往来如梭一派繁忙景象。有专供乘客的机动船,叫“班船”,木船也可以坐,但是只能坐熟人的,很不方便。所以,你听人们与来客打招呼往往是这么两句:问“咋么来的?”答“起旱嘛”。
“放账不如泡面”,借粮食给别人是行善的事情,可是因为不宽余,还可能有借难还,所以“放帐不如泡面”。泡面?面条的发胀好,多泡一会,泡的宽宽的,哄哄肚子,比借出去稳当。
“瓜菜代”,顾名思意,粮食不够,瓜菜代替。可不象今天,吃瓜菜成为时尚,比粮食贵。那年代,粮食歉收,瓜菜却出奇的好,青头萝卜可以长到十斤重,冬瓜可重达上百斤。但是,缺油少粮,把它做主食,三天就叫人受不了,现在提起萝卜米汤,顿顿冬瓜,还令许多中年人有“晕”的感觉。
“救济粮”,现在还存在救济粮,但是使用的范围和粮食的内容已经大不相同了。那时救济的范围很广,粮食也以玉米为主,当然和东北高粱米、河南干红苕片子相比,玉米是好粮食。
即使是河南的红苕片子,拿去学校做点心,慢慢嚼,也是甜丝丝的——比饿肚子强多了!
岁月不远,却一去不回。这些困难岁月的语言,正在从我们的口头消失,只留存于我们的记忆之中,立此小文,以示怀念!
消失了的饮食
麦砬子,属于刨青的吃法,麦子还没有成熟,但是粮食又接不上,人们只好把只有六七成熟的麦子收回来,放在石磨子里只推一道,成为半碎的粗粒,下锅煮熟,样子和拌汤差不多。吃来有新麦的清香,而且是连麸皮一起吃的,比较节省。
捡地钱,地钱属于真菌类,夏天阴雨之后出现在草地上,样子象木耳,青黑色。捡回去用水洗净,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和韭菜蒸包子,这个味道最好,现在大约已经没有人吃这个东西了。
麦豆酒,新麦收获后,蒸熟,晾冷,拌上酒曲,酒气来后兑入凉开水,不几天,麦豆酒就做成了,其味酸甜可口,又管醉又管饱,至今令人回味不已。
糖稀酒,八九月红苕收获季节,就可以做糖稀酒。把红苕蒸熟,捏烂兑水,用豆腐包过滤,渣喂猪,液体下锅熬开(如果继续熬下去,水气熬干就是红苕糖),晾冷,放入酒曲,就可以做成糖稀酒,酒度数不高,做的好了,甜酸适度,做的不好,只酸不甜,那只有在喝的时候放一点糖精,至于糖,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舍不得的。在山区、浅山区家家户户都有一大缸,来了亲朋好友,过年过节,就可以对付了。由于酒度不高,大约只有十几度,是拿碗来喝的,又有一点甜味,这容易使喝酒的人大意,所以被撂翻的人也不少。
红苕酒,是高度酒。烤红苕酒一般是在冬季。把红苕蒸熟,晾冷,捏烂,拌入酒曲,经过几天发酵,有了酒香,就可以上甑烤酒了。先烤出来的是头曲,接下来是二曲,最后是尾子水,尾子水是淡味,要和度数高的头曲勾兑来喝。小孩子很喜欢看烤酒,主人请品尝也不推辞。我有一次在邻村一个好朋友家看烤酒,头曲出来了,主人说:“尝一点”,喝两杯;二曲出来了,主人又说:“你尝这个”,再喝两杯,三下五除二,我就找不到东南西北了。最后是姐姐把我背了回去。要说明的是,那个年代,烤酒没有商业目的,是自己来喝或者馈赠亲朋。卖是不允许的,“浪费粮食”、“投机倒把”随便找顶帽子就把你的资本主义尾巴割了——轻者没收,重则开你的批斗会。还是自己喝保险。
说了五样,酒占了三样。为什么?那个年代,酒是限量供应不说,老百姓还不一定买得起。一个劳动日到年底分红,我们村是八毛钱,这是好的,因为我们村办的有养猪场、豆腐房。有的村只有几分钱一个劳动日,就算是八毛,一年你全劳动了365天,也才多少?两三百元。许多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年终决算下来,还欠村上的钱,叫做欠钱户,相反就是余钱户了。这酒啊,回忆起来,还真是带着令人伤心的酸味!
民 居
对岚河口 的记忆,我停留在七十年代末。那时的住房,以土墙瓦屋为主,还有一部分草房。砖房一般是机关单位才有的,普通人家的砖房,如 洪家院子、谢家院子,都是旧社会修建的,青砖。
在旧社会,岚河口有谢( 谢英武,人称五老爷 ),罗(罗福成,做过岚皋自卫团团长),郭(郭家三),唐(唐德银)四大家族,其中郭唐两家住所不在岚河口,作为安康县的一个 区,区机关的办公用房多征用谢罗二姓的砖房,如区公所用谢家的,银行用罗福成的,岚河中学建在罗家祠堂,也是罗福成的。只有岚河小学建在镇江寺, 这是公益建筑,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建 寺的目的是为了镇住那年年肆虐的汉江洪水。解放后,直至七十年代末,公私建筑,砖房很少。
土墙瓦屋,原料是黏土,木材,泥瓦,用石头为根脚,以墙板筑土,盖上泥瓦,最为常见。至于草房,与瓦房的区别在于苫盖材料是草,虽然那时的泥瓦不过三分钱一片,也有用不起的,只好用草了。草有两种,盖牛圈猪圈的,用麦草,只能管几年,草就会腐烂;盖住房的用我们当地人叫做“扎锥草”的一种草,这种草长在山上林灌之中,单独长成一兜一 兜的,长约五六十公分,茎干很硬,耐腐蚀。种子有长长的芒,绊 到衣服上就往里钻,所以叫 “扎锥草”, 这种草苫盖的房子能管十几年。用专用工具苫盖的新草房 ,一尺多厚 ,看上去很整齐。草房冬暖夏凉,造价低廉,缺点显而易见——不耐久,怕火。新房子当然很整齐,过上几年,上面会长青苔,狗尾巴草,年代再久了,会出现破洞,这时,主人如果还不能换泥瓦,那就又要 上山割草,重新翻盖了。
如今的故乡,这种草房已经没有了。可是如果哪个农家乐盖一点这种房子,到是别有一番风味,只是好象没有人这么做。
古庙和道观
岚河口的古庙和道观,大的有三座:龙王庙、镇江寺和清凉观。我们记事的时候正置文革后期,庙里早就没有了神仙塑像,和尚道士也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洪流中还俗回家了。只是空下来的房屋用途各不相同罢了。
龙王庙,七十年代时已经没有了龙王庙的正式称谓,只是叫做王庙嘴子,归粮站所有,庙里是加工厂,庙外的拜台正好用来晒粮食。老先人们在这个地方建立龙王庙是很科学的,为什么呢?这得先看岚河口的地形,清凉观那里是一个山垭,呈东西向,垭西面是汉江河,垭东面山脚下就是汉江的侄女石湾,山势从那里绵延向东南十几里,形成一个半岛样子,汉江沿着半岛奔向东南,就在王庙嘴子这个地方一个大回转,折向西北。在我们记事的年代,龙王是不拜了,可是龙王庙下的水箭却是年年要修的,把水箭向河南,河北的土地就少受损失。岚河口的千亩坝地的形成正是得益于先民对这种地形的利用。
镇江寺,从镇江寺这名称就可以看出,建 寺的目的是为了镇住那年年肆虐的汉江洪水。解放后,这里做了岚河口小学的校舍,所以尽管我的一年级就是在大殿里上的,却没有见过神像。现在按我的推想,庙里面供奉的应该是大禹。虽然上河有龙王庙,但是龙王和洪水是一家人,求的再好,总是靠不住。大禹专门治水,应该有此神力镇住汉江洪水。然而,在我们的记忆里,也许是禹王已经不在镇江寺的缘故吧,大洪水来了,除了淹没不了这座古庙,整个坝子还是一片汪洋。
清凉观,是道教坛场,地处岚河口到流水店的交通要道。那时侯道观里和别的庙宇一样,没有了三清诸神,只有空荡荡的房屋,大门也不用锁,行人到是可以进去避避雨什么的。别的嘛,因为地方偏远,没有挪作它用。到2003年,我回去老家一趟,那当初热闹的王庙嘴子和镇江寺都一并做了龙宫水底,只有这清凉观还在,只是依然没有神仙入住,用做了公房。
古庙道观,作为岚河古镇人文历史的载体,几经变迁,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地位。如今,龙王庙和镇江寺已经淹没了二十多年,清凉观看来也永远难以恢复它道观的本来面目了。再过几十年,随着我们这些人的老去,记忆也将永远消失。趁如今还不糊涂,撰此小文,聊作纪念。
古树
在我小时候,总以为,那棵见惯的、古老的皂角树很平常,它就在古道边,自我们记事时开始,天天看见它,常常在树下乘凉、捡皂角、和伙伴们玩耍。在我们心中,它本来几有,似乎也永远不会消失。然而,当我走了很多地方以后,我才知道,这样大的树是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非常罕见的。而且,由于库区淹没,它竟然消失了。消失的那么彻底,没有留下照片,也没有文字资料。
这个巨大的皂角树长在清泉四队隔坡上(这是地名,农村地名都不讲究),主干有两人多高,树围四个大人牵手合围也围不下,树冠巨大。在还没有公路的时候,树下就是通往岚河街的大路。它生长在一个 干石坡边,地势险峻而且贫瘠,也许正是因为生长在这样的地方,才使它树龄千年而未遭砍伐。
听大人们说,这棵树在唐朝就有了,黄巢在陕南流动作战时,这树上还留下了起义军的宝剑。问大人为什么现在看不见?回答是,一千多年,早就长在树里面去了。小伙伴们听说后,也有身手矫健的爬上去,却没有看见什么宝剑。我当然也想上去,可是我小时候是罗汉肚子,爬细树也是肚子先靠拢树干,爬不了多高。这么粗的树就更加无法下手了,只好望树摇头,玩其他的去了。
皂角树是有刺的,而且树刺之大,我所见过的树刺无出其右。有一年夏天,我们在树下游戏,玩的忘情,我一脚踩在一棵刺上,刺尖断在脚后跟里面。我哇哇大叫,哭声震天。住在这里的罗家表婆一家,忙了好几个人为我挑刺,挑断了三根大针,才把刺挑出来。罗表婆家在当时算是我们那里的殷实之家,我们常常玩忘记了,就在他们家吃饭。只可惜好心的表婆后来竟然得了绝症,痛苦离世,叫人叹息不已!
古老的皂角树,矗立道旁,历经千年风雨,见证了王朝兴替,古镇兴衰。多少英雄豪杰消失了,多少坚固的建筑倾颓了,它却依然生机勃勃,倾听汉江的波涛,诉说着岁月的悠久。可是为了国家的建设,古树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当时,岚河口没有照相馆,就是有,也没有人会意识到为古树拍照留影。这是岚河人永远的遗憾!
所幸的是,在汉江河南面,还有三棵古树,因为地势高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大、中、小桦栎树,三个地方的地名也因此分别叫做大、中、小桦栎树。
从王庙嘴子渡口过河,经过玉岚公社驻地上方,过五里砭不远,就是小桦栎树,它比水桶粗些,树干上布满青苔,还有寄生木。据说这寄生木羊如果吃到了,死的时候就会闭上眼睛,死而无憾。小桦栎树下是荒地,我们小时候在那里打过猪草。再往前走就是中桦栎树了,它比小桦栎树粗一倍以上,这里林木也多起来了。
大桦栎树最雄伟,这里地势开阔,它象一把巨伞撑在森林的边缘。树围树冠竟然比岚河口的皂角树还大的多,令人肃然起敬。不知道现在这里是不是作为旅游资源开发了.
几年前,我在《安康日报》上看到署名文章,呼吁建档保护这三棵古树,我虽然忘记了此人的名字,却对他悠然而生敬意!终于有人认识到了古树的价值,这也算我的遗憾中的欣慰吧!
移民
这里是一组数据:安康县总共移民11620。其中岚河、流水分散安插1642人,恒口安插997人,五里安插1866人,关庙550人,文武乡75人,县境内零星安插269人。
出县远迁3757人。其中汉中(城固)900人,关中(周至)540人,湖北鄂州地区(主要在长港农场)400人,襄樊(随阳农场)400人,洪湖地区200人,湖北省其他地区200人。
山东、河北、甘肃、新疆、四川、北京以及本地区岚皋、镇坪、紫阳、汉阴等地分散落户约200人。
数字是枯燥的,这一串串数字后面是一万多鲜活的、难离热土的人。
1979年暑假,我的好友,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洪元平一家首先迁移到镇坪,他爸爸在那里工作。是年11月,我们一家六口(祖父母、父母,我和妹妹)迁移到岚皋,大哥已经在此工作十余年。我们两家搬迁的最早,离85年下闸蓄水还有六年。无论如何,搬迁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的河北大队的老乡们,他们在岚河的条件是最好的——当菜农、吃供应粮。他们吵吵嚷嚷了好几年:要搬迁就集体搬迁,决不分散零迁。可是,有哪一个地方能同时容纳近千人一个大队?他们还是被分散搬迁了。他们对分散搬迁的那份担心我当时理解,搬迁后体会更加深刻——势单力薄、可能被人欺生,这,是实实在在的。当然,许多老乡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都融入了当地社会,安居乐业。最可怜的是迁到江汉平原的一批人,其中有我熟知的艾德兆表叔,他在我们当地有杀猪的手艺,为人孔武有力、刚直义气,很受人尊敬。就是这样一条硬汉子,不几年,竟然哭着跑回了岚河——那里地太宽,种不了,负担又重,又受人欺负,钱被弄走不少。于是抛舍家业,把仅剩的一点钱绑在裤腰带里,逃难似的回到岚河。我在听说这些以后,心里酸酸的,好想哭!
故土故土,一方热土;祖祖辈辈,亲朋故旧。这一切,当初不感觉,在失去了以后才真正明白了它的意义和分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