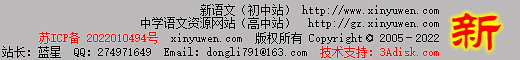村边那棵柚子树
老家村边有棵柚子树,村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栽种,什么时候开始结果的,但谁都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枯萎,什么时候死去的。柚子树活着,谁也不觉得它有多少特别,就像每天升起落下的太阳一样;就像抬头见山低头见路一样;就像村前村后那一个山头连着一个山头的树木一样,自然实在。柚子树死了,人们却常常议论到它,勾起许多回忆,许多思念,咀嚼、回味着柚子的酸楚、苦涩、甘甜、芳香。我怎么也没想到,那棵柚子树的死去,在我心灵的祭台上,引起了多少的裂痛、悲伤、愁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裂痛、悲伤、愁绪,大有与日俱增之势,挥之不去,抚之不平。
老家村庄在山旮旯里,终年累月被大山夹裹着,二三十户人家。村后,靠着逶迤的群山,村前,门对青山廓外斜,一条小溪汩汩而过。房前屋后,茂盛地生长着丛丛修竹,给村子披上绿色的生命。两排大批促大干年代建的集体房,今天看来虽然明显带着那个年代的痕迹,但也说明这里的人们那时拒绝“专政”和“斗争”,还真的大干了一番!小山村很秀美,但谈不上什么特殊,那棵长在村边一个高高的土台上的柚子树,便成了一个标志,一道风景。春天,雨水潇潇,柚子树花开,走在村头村尾,都能闻到柚子花浓烈的清香。夏天,烈日炎炎,柚子树枝繁叶茂,人们工余饭后,常围在柚子树下纳凉唠嗑,享受着山里的宁静和农人的悠然。秋天,金风爽爽,柚子树上挂着一个个小灯笼似的果实,圆溜溜,黄澄澄。冬天,山风呼呼,柚子树傲然顽强,丝毫没有畏惧的模样。有时,淘气的小孩子三五成群,爬上树梢,摇晃着,嬉闹着,唱着山歌,给僻远的山村增添了生命的活力。
柚子树下,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动感鲜活激人情怀的故事。
那一年,正是极左路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极左路线的爪牙们,三天两头进村割资本主义尾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村子里的人自有对付的办法:每天安排一个人到树顶了望,一声“鬼子进村啦”,家家户户立刻就把圈子里的猪赶到后山,把院子里的鸡鸭收笼放到野外,避开了“割尾巴”。贫穷的农家,就靠着这些牲畜收入,供小孩上学,换油盐酱醋。
那一年,村东头的阿山家遇到天灾人祸,一连几天的暴雨,山洪冲毁了他家的承包地,一季粮食绝收了。阿山上山砍柴,本想挑到镇上卖几个钱,不料又被毒蛇咬了一口,几个月没能干活,家里一下变成贫困户,眼看就要开学了,没钱给小孩交学费。村民小组长叫人把柚子摘下卖钱,解了阿山儿子上学的燃眉之急。村西头的阿海生病了,一连几天发高烧,嘴里苦涩得难受,几个小朋友听了,“噔、噔、噔”爬上柚子树,摘下一只大柚子,送到阿海床前,又甜又酸的柚子肉使阿海有了食欲,病情一天天好转。
不清楚从哪一年哪一天开始,有自私的人收工了,图一时方便,把老牛拴在柚子树上,那老牛身体经不住蚊蝇叮咬,不断地在树干上磨蹭,可怜的柚子树被磨破了皮,汁液一点一滴地渗出,就像一点一滴地流血,一点一滴地流泪。有顽皮的小孩子上山砍柴,在树下玩耍,常常在树干上试刀,留下一道道刀口,柚子树忍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创痛。有贪婪的人看到柚子挂果,从果皮还是青青时,就开始上树采摘,挂在树梢末的摘不到,就用竹竿打,打得叶子扑籁籁地往下掉,有的干脆把整条枝梢砍下。终于,古老的柚子树,经不起蹂躏、摧残,树身干裂了,枝丫少了,叶子枯了。
我在外读书,在外参加工作,但难解故土情结,每年都要回老家几次。过去,离村子很远,就能看到那棵柚子树,就像船在大海航行看到了航标灯。后来,远远的看不到那棵柚子树,总觉得少了点东西,心里涌动着痛楚和惆怅。每次回到老家,我都要登上村边的土台,祭奠死去的柚子树,遥想着,思考着。这柚子树虽然死去多年,但还有二三米高的树干依然仄立着,历经风吹雨打日晒,不倒不朽。这柚子树怎么啦?传说北方有一种树叫胡杨,这胡杨有三个一千,活着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可从没听说柚子树有三个一千,哪怕三个一百。柚子树,你是在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还是在作最后的命运抗争?或是苍天的刻意安排为的是警示后人?柚子树,不需要责怪给你带来厄运的人!那个时候,谁能有什么环保意识?谁懂得爱护自然?谁知道那叫践踏生态?不是连成片的原始森林都砍伐殆尽吗?不是年复一年的非洲干旱、亚洲水害、北美洲大森林火灾吗?柚子树,你虽然死去,但你以自己的死亡为代价,唤醒了许多人的良知。今天的人们,普遍增强了生态环境观念,即使在这山旮旯里的农民,也已经懂得保护树木,保护环境,建设绿色家园!柚子树,你九泉有知,可以抚慰自己死而无憾,昔日村子四周被砍伐、被火烧得光秃秃的山头,又恢复了先前的葱绿。举目四望,处处青山,杉木林、松树林、洞叶林、毛竹林、果树林,郁郁生机,充满希望。“春风又绿江南岸”。
柚子树,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