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 新语文 >> 企业管理 >> 资本营运 >> 企业改制 >> 正文 |
|
|||||
| 明晰产权与规范政府 | |||||
|
作者:佚名 人气:447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
|
[摘要]放权让利改革的这种结果显然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有关。因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还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政府履行其行政管理职能的方式尚无根本变化,政府直接控制企业仍然被当作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方式之一。而且,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国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仍占有很大比重,维持国有经济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和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至关紧要。另外,国有企业还替政府承担着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职能,在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未完全确立起来之前,国有企业难以摆脱这种社会职能,这也成为阻碍国有企业按商业化原则运营的重要因素[8]。所以,即使到了九十年代末,中国政府仍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维护国有部门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这一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国有企业的总资产中由国家出资构成的份额不断下降。这一点在我们的1251户企业样本的数据中清晰可见。我们计算了这批样本中国有企业的国家资本比率(企业总资产中国家资本所占的比重)。表1.是计算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1994~99年期间,样本中516户国有企业的国家资本比率平均值从22.25%下降至1999年18.80%。 表1:国有企业的国家资本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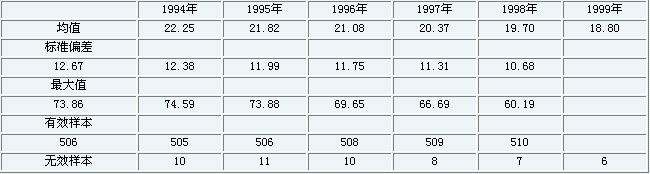 说明:国家资本比率=国家资本额÷资产总额×100 为了进一步推断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国有资本比率,我们对表1.中各年的国有资本比率均值作单样本T检验,以估计样本总体中国家资本比率均值的上限。表2.是估计的结果。它显示,根据这批样本企业的国家资本比率均值推断出来的总体均值上限也在逐年下降,从1994年的24.0%下降为1999年的20.0%。 表2: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国家资本比率上限(1251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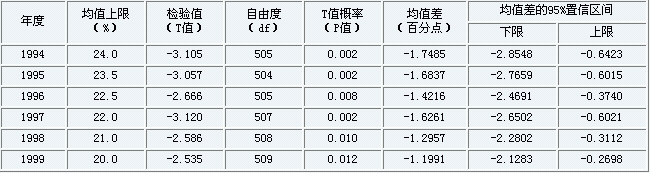 说明:单样本T检验;双侧检验,95%置信度。 需要说明的是,这516户国有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有165户,占32.0%,中型企业有280户,占54.3%,小型企业有71户,占13.8%;大中型企业合计占样本中国有企业总数的76.3%。显然,这个样本在企业规模结构上明显偏向大中型企业,而这类企业中的国家资本比率一般应高于小型国有企业。所以,可以进一步推断,在全国的国有工业企业整体中,平均国家资本比率只会比上述推断结果更低,在国有企业整体的企业金融中,政府财政的作用已趋于淡化。 三、财政收入与国有企业收益的疏离 国家所有权在国有企业产权安排中的另一个体现是财政对国有企业的收益索取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统收统支”的制度,企业方面在收益的分配和处置上无任何自主权。这意味着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者,它既享有国有企业的全部盈余,也承担着国有企业的财务风险。 八十年代初以来,国有企业从利润留成制、利改税、承包制,再到1994年税制改革,经历了一系列收益分配制度上的改革。这些改革虽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共同的制度取向,即在扩大企业收益自主权的同时,使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从政府转向企业成员。 各种形式的利润留成制始于七十年代末,其基本思路是将企业成员的个人收入与企业盈利水平挂钩,以调动企业成员扩大企业盈利的积极性。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利润留成率难定,以及激励作用上的“棘轮效应”等因素,各种利润留成制的激励效果远未达到政策设计者的预期目标,还导致国有企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不断下降。据统计,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中上交利润的比重从1979年的70.1%下降为35.08%[4]。 针对这些问题,中央政府开始考虑以“利改税”取代各种利润留成制。利改税的基本构想是以企业所得税的形式固定国家获取企业利润的比率,在此基础上,允许企业自主支配税后利润,而国家财政则不再为企业提供资金和弥补亏损。然而,企业向国家缴利润是国家作为企业所有者享有企业盈余的表现,同时也意味着国家负有为企业承担亏损的责任,它体现了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内涵。而国家向企业征收所得税则是国家凭借行政权力征取企业部分盈余的行为,它是国家对一般商务主体行使强制权力的体现,国家并不因此而为企业的盈亏承担责任。这两种收益权的性质完全不同。 从1983年6月1日起,利改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利改税没有根本改变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实质关系,但它第一次试图限定政府获取企业收益的权利,弱化财政收入与企业效益状况的关联度,因而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演变中一次重要的概念突破。它意味着,政府获取国有企业收益的权利开始向非剩余收益权转化,政府朝着摆脱国有企业剩余索取者身份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利改税推行时间不长,就遇上了财政状况连年恶化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这迫使政府再次强化对企业收益的征收(调节税成为这种征收的手段),利改税的初衷归于流产。为摆脱财政困境,政府从1987年起放弃利改税,转而在国有企业中全面导入了承包制。 从形式上看,承包制是使国有企业从交税退回交利润。但现在来看,承包制实际上是推动政府收益权非剩余化的又一重要阶段。因为,承包制只在企业新增盈利部分保留了按比例上交财政的分配办法,而作为承包基数上交财政的那部分收入是事先议定的,与企业盈利水平无关。这就使国家从国有企业获取的收益被进一步租金化了(有的地方,甚至连新增收益的上缴都实行定额包干[5])。所以,从政府财政收入与国有企业盈利状态的关联程度来看,承包制延续了利改税的制度取向,切实地推进了企业收益与财政收入的疏离。 承包制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自由度,但承包制在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一对一谈判的基础上确定承包合同,无法克服企业与政府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广泛实施承包制的几年中,企业收益的分配向企业成员倾斜的问题日益突出(董辅礽、唐宗焜,1992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侯荣华、康学军,1995年)。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政府在1994年放弃承包制,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分税制改革。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彻底地实现了国家对国有企业收益权的租金化。因为,它将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基础从企业利润转向企业的销售收入,使与企业盈亏无关的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对企业盈利的收益权则基本上留给了企业。 表3:八十年代以来财政与国有企业间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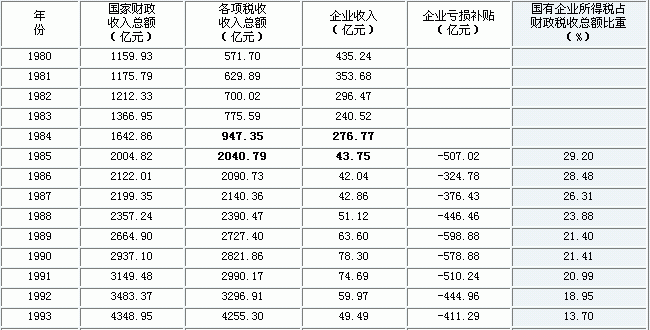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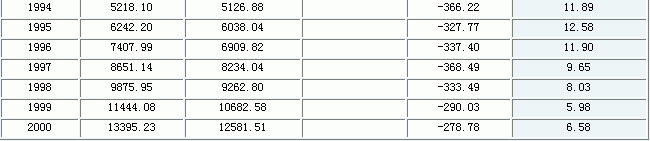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01年) 表3.清晰地显示了八十年代以来国家财政与国有企业关系中的这一转型过程。在1980年时,国家财政收入中来自“企业收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部分为435.24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总额的37.52%。但从那以后,“企业收入”所提供的财政收入不仅在相对比重上、而且在绝对数额上都迅速下降,而财政收入中的另一主要来源,“各项税收”的数额和比重则不断上升。如在1980~84年期间,国家财政收入中各项税收的数额从1980年的近572亿元上升至1984年的947.35亿元,年均增长13.46%,而同期的“企业收入”则从435.24亿元下降为276.77亿元,年均下降10.70%。然而,这还只是这一转型的序曲,1983年开始导入的“利改税”进一步推动着政府财政收入与企业盈利的疏离。在表3.里,税收总额在1984年时为947.35亿元,而1985年却跃升1.15倍,变为2040.79亿元;同时,体现企业利润上缴的“企业收入”总额却缩小84%,从1984年的276.7亿元跌至1985年的43.75亿元。一年之内出现如此大幅度的变化当然不可能是经济流量本身变化所致,而应视其为“利改税”的后果。由此开始,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重要性逐年下降。进入九十年代后,“企业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日益式微,而1994年的税制改革更是使它从国家财政收入的统计中完全消失--由此,财政收入与国有企业的盈余基本脱钩。 表3.中还有一项数据的变动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国家财政与国有企业盈亏状况的疏离过程。那就是“企业亏损补贴”的推移。它显示,1985年时,财政支出的企业亏损补贴总额有507.02亿元,但到2000年时,这项支出的总额减少为278.78亿元,下降了45.02%。然而,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和亏损面是不断扩大的。如据财政部统计,198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额是417.1亿元,到1998年时增长为3066.5亿元,2000年有所下降,但仍高达1846.0亿元[6]。一面是国有企业的亏损额连年递增,一面是财政对企业的亏损补贴不断减少,这只能说明,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亏损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少。 另外,据《中国财政年鉴》披露[7],从1985年至2000年,国家财政税收总额从2040.79亿元增至12581.51亿元,年均增长12.89%,同期国有企业的所得税从595.84亿元增至827.41亿元,年均增长2.21%,远远低于税收总额的增长速度。这使国有企业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总额中的份额不断下降(表3.)。所以,即使将财政向国有企业征收所得税理解为财政收入与国有企业的盈余仍有关联,这种关联的程度也是逐年下降的。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企业所有者就是企业的剩余索取者,它既有权利享有企业的盈余,也有义务承担企业的亏损。而放权让利的改革解构了财政为国有企业承担经营风险的经济基础,国家不再为国有企业承担经营风险了。因此,从现代产权理论出发考察国有企业在收益分配方面的演变,可以说,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中期已经开始。正如张维迎(1999)所指出的:“‘放权让利’的实质是将剩余索取权和经营决策权从政府转移给企业,……。” 四、国有企业制度中的非经济性层面 然而,“放权让利”是一种不彻底的产权改革,因为它没有使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严格起来,更没有实现政企分离。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制度结构中含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经济性层面,即政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为企业提供资金、控制企业经营并承担企业的盈亏责任。这在制度上主要体现为企业资产的国有制和企业财务运作上的“统收统支”。另一个是行政性层面,即政府作为社会的行政管理者,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实施一元化统制,它规定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能并控制企业的运营。这在制度上主要体现为企业对政府行政系统的组织隶属,如企业被赋予行政级别、企业经营者的人事权归上级政府或党组织控制、企业经营必须服从政府的行政指令和工作计划,等等。行政层面的制度安排也是关于权、责、利的界定,但其社会内涵和作用机制是非经济性的,与经济层面的制度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只淡化了政府作为资本所有者对企业的经济性控制和责任,却迟迟没有触动政府作为社会行政管理者对企业的行政性控制和保护。由此而来,随着放权让利的展开,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企不分越来越不具有经济属性,而演变为一种超经济性的行政垄断现象。 例如,从名义上来讲,实行“拨改贷”之后,银行与企业间的信贷活动属企业行为,应由银行按商业化原则行事。但实际上,国有银行受制于政府,无法严格按商业化原则对国有企业放贷,国有企业也可以无视资金成本和风险地向银行索取资金,使用资金。因而“拨改贷”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疲软依旧,企业对于银行贷款的“饥渴”与过去对待财政拨款的态度如出一辙。 进入九十年代后,政府在满足国有企业的“资金饥渴”上又多了一个新手段,那就是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但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独特结构,资本市场在公司治理中应有的控管作用难以生效,高速发展的资本市场只是为国有企业开辟了一个新的无风险融资渠道(民间俗称“圈钱”)。 这样,在“统收统支”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主要以政府财力为基础,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要靠财政资金来满足,国有企业的经营亏损要靠财政补贴来弥补。但进入九十年代后,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转而依赖民间资金,国有企业的财务亏空主要靠银行信贷资金和证券投资资金来填补。这所以可能,都是因为政府对国内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领域实施了全面的行政统制。 又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可以从计划、供应、销售、价格等多个方面对国有企业的运营施加控制,但放权让利的改革使政府在这方面控管企业的手段越来越少,因而从行政上控制企业经营者的任免权成了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主要手段。即使在九十年代末,多数国有企业在资本产权关系上已与政府没有多少关联,但多数国有企业的主要经营者依然要由政府主管部门或上级党组织来任免。表4.是利用“数据800”做的一项分析。它显示,迄1999年底,在这800户样本企业中,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99.77%)在高级经营者的任免上仍要受党组织的影响,其中回答“影响很大”的企业占样本中国有企业总数的42.73%,远远高出其他各类企业。仅此一点就足以决定国有企业难以成为纯商业化的经营组织。 表4: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主要经营者任免上的影响力(应答企业数的分布) |
|||||
| 财富论今——新的理念 心的飞越 | |||||
| | 设为首页 | 劳动创造一切,财富造就神话 | |
| 财富论今-http://cf.xinyuwen.com 苏ICP备05013302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