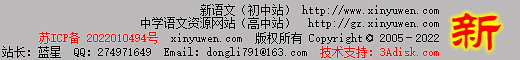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有时真是繁琐到了无聊的地步,很多文章被弄得是“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如初中教材《范进中举》,一篇短文,教师讲时代,讲科举,讲讽刺,讲势利,讲来讲去,看似头头是道,其实是人云亦云,不懂装懂。学生是看得眼也花了,听得头也晕了;就是这时,只听见铃声响起,于是一窝蜂地急着跑出去玩耍,哪里还管课文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对于初中生来说,《范进中举》只要学生一看完,教师两句话就讲通了:没有中举,范进是个“孙子”;一旦中举,范进是老爷。
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从胡屠户的言语行为在范进中举前后的对比上就可一目了然。
范进中举前,胡屠户的言语行为是这样的。
范进因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那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城里张相公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内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向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门不着。
中举后,胡屠户的言语行为是这样的:
(范进)见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来骂。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敢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老爷,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么?我时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范举人先走,胡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著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
这是多么简洁明白的文本啊!前后一对比就什么都有了,还用讲吗?
如果不是把人往糊涂里整,我真是不明白,就文本的理解而言还能讲出什么来!
以上是对《范进中举》一文的普及型理解。
当然,真是想往深处讲还是有内容可讲的。那就要把眼光放远到整个社会中去。
那就可以深入地研究一下范进发疯的本原意识,讲讲《范进中举》一文所体现的科举制度对中国文人人格的解构与重构。
范进因中举而发疯,可以说是原有人格被解构而新的人格未被及时重构的外现。当然要论述这种解构,就要说一说中国文人普有的二元意识,就要说一说中国所特有的二元文化。中国的文化有两种对立性很强互补性也很强的载体,一种是儒家文化, 一种是道家文化。从汉代开始,儒道两家文化几乎同时形成规模,然后并驾前行。但是,儒家文化要求入世,讲究修身齐家平天下,要求人的利益服从于社会(政治)利益,这就必然形成中国文化中凝重不堪的官本位意识。道家文化出世,注重人自身的存在,认为个性的张扬是人的根本幸福,这就必然形成中国文化中人本位意识。
民族文化的这种意识截断,必然造成文人的人格分裂。最典型的是李白。
李白的生命中就充满着个性张扬和功名富贵不能兼顾的痛苦。当功名看似唾手可得之时,他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当他获得了很好的机会,径直来到玄宗的身边时,他发现,他的天才也就是用来写一写“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之类的消遣诗时,而他自己在玄宗眼里只是一个玩物时,当他发现他的功名富贵需要用他的人格去换取时,他受不了。于是他衣袖一拂,高昂起尊严的头颅,飘然离开了玄宗,也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富贵,他高唱“安能摧眉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当然,离开京城他发现他个性的张扬和功名富贵依然是是不可兼顾的。他的痛苦于是更深,他无奈地呻吟了,他吟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后来有个传说,认为李白死于醉后捞月溺毙。虽然过于浪漫和传奇,但我觉得想象出这种死法的人对李白是了解的,在李白的知音中应排第一!因为,这种浪漫和现实才真正能够反映李白的人格在对立中的分裂和人生价值的失落。
到苏东坡,苏东坡的特殊经历使他以儒家入世的思想应付成功,却又不得不以道家出世的思想来安慰失意。于是他“达则兼济天下(儒),穷则独善其身(道)”—— 在他这里儒道似乎被完美地合二为一了。从此,中国文人们似乎觉得他们可以在人格缺失的社会中游刃有余地生存而不必担心人格的分裂了。所以,他们给了苏东坡以过高的赞扬和歌颂。
其实不然。苏东坡的儒道两学并没有在他内心的大道上并行不悖,他的道学其实只是儒学的一种无奈的补充,是一声儒学的感叹,一种扭曲,一种变异,在他的内心他还是以儒学的入世思想为体的。我们看他的作品就知道了。仕途顺畅时,他的诗歌就表现出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
诗歌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这中间的太守多么得意洋洋,虽为“老夫”却表现出“少年”一样的狂放,一名文职太守,却要“亲射虎”,而且向孙权看齐!这是多么豪放和酣畅啊!
文章如《喜雨亭记》: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系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于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你看,下了一场雨,又赶上自己所建的亭子落成,就高兴得不得了,认为比下了珍珠和宝玉还要好,说民众把这归功于太守(就是自己),自己把功劳归于天子,天子把功劳归于造物,造物归于太空,太空空荡荡,不太容易命名,于是干脆命名了自己的亭子,功劳归来归去,归到了自己的亭子上。体会一下作者是多么地自得和兴奋。
当然,这一诗一文都是以太守身份创作的。所以这些得意也就是当官的得意。
如果无官做了,那就是另外一种口气。如《前赤壁赋》中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从字面上看是无比地旷达与轻松的,然而骨子里却是“吃不到葡萄只有说葡萄酸”的痛苦。正如他的歌吟:“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这首诗歌的基调应该是很放达的了,可是文句中了讲得很清,要想“不辞长作岭南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日啖荔枝三百颗”;如果不能呢?那怕就是恕不奉陪了。这一肚子酸气憋得不行,一汪泪水难以流出,只好憋回心室,露出一脸苦笑。而现在很多人就错把这苦笑当成欢颜。
所以,苏轼的潇洒是装的。其实是没官当的痛苦。
不过苏轼的潇洒装得格外真诚而美丽,所以后世的人们在有了类似于他的遭遇时也需要像他那样装,最后,苏东坡的名声就空前大了。
所以说,范进因中举喜而疯,李白因不用怨而狂,苏轼因贬官惧而逃,表现虽然各异,其实质都是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比量于官场的成功与失败。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就这么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人的心目中。
当然,这种思想的产生是有其社会背景的,这个社会背景就是中国文人做官则八抬大轿,黄金美人,不做官就一无是处,所以在中国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格言,“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也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警言。书生的有用与无用,全在于皇帝的重用与否,重用了则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不被用则一无用处。其实不管用还是不用,归根到底中国文人都是被动的,都没有独立的人格。
这种情形在中央电视台《康熙王朝》中姚启圣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姚启圣,鄙视满夷,拒不合作。荣华富贵难动其心,艰苦磨难罔动其志。针对他的“非暴力不合作”,康熙在万般无奈之下,以蛮治之:不问罪,先关入监狱,酒菜招待;但是不审议,不定罪,因为他本无罪;尤其是不给他书,没人理,让他在无聊中过日。六十天下来,姚启圣“盛”气消落;回京路上,康熙又把他放在冰天雪地里一冻,姚启圣“圣”气也消落。这时间,康熙让他进入暖轿,一本杂书,一碟剩点心,康熙脚下一个角落,他姚启圣就知道感激了,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康熙脚下的顺民进而成为顺臣了。而一旦为康熙所用,他就立即提出了平定台湾的方略“三可剿”“三可抚”,恩威并施。于是被康熙授与平台大权,从而成为平台的风云人物。
其实中国文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为人所用,或者说为人所不用。用时可顶天立地,成宏伟大业;不用,则仅是养马匹夫,粪土不如。姚启圣的命运转变我觉得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人的两条思想局限。其一是“士为知己者死”;其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被许多中国文人奉为圭臬的话语看起来是富丽堂皇的,确实也支撑起了中国文人的笔挺的脊梁,但是它同时也取消了中国文人独自站立的资格。你看“士”是要为“知己者死”的,它就是这样直接地、明目张胆地取消了“士”的独立资格。而什么是“达”呢?达就是有“人”赏识;什么“穷”呢?穷就是没人赏识。总之一句话,“士”的命运总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可以说,在“士为知己者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窠臼中,中国文人自己放弃取得独立人格的可能。
当然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缺失的另一原因是缺少社会支撑。传统家天下的封建社会对于言论不是采取支持和鼓励,而是采取镇压与禁锢,所以在中国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非常有名的小说甚至也要为谁是它的作者而争论不休,因为作家写了小说往往不敢承认,弄不好就有文字狱,杀身之祸,抄家之灾;版权的保护更是从不提及,这又使文人缺失了经济自立的条件。无论是精神和物质中国文人的脊梁都缺少社会支撑。
人格的彻底缺失最终把中国文人的价值追求全部逼仄到仕途之上。所以,范进中举就会高兴得发疯。因为,中举使他从“孙子”一下子上升到“老爷”,从没有基本的人格而直接有了高贵的官格。一个人面对如此的命运巨变不发疯才奇怪。
说到底是一个人权问题,在人权没有保障的社会,即使是有一两个敢于直言宁死不屈的人也往往被无声无息地弄死,同时这种毫无价值的死亡让人连死的勇气也缺乏。我曾经听说文革中的烈士张志新在被执枪毙前先被割断了喉管。这个虽然是传闻,但是我相信。因为中国有产生这种残酷情形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任何勇敢的人都要注意说话的风险。一个勇敢的人可以不怕死,但是没有人不怕毫无价值地而且无声无息地死掉!
然而,一个社会,文化人没有人格,整个社会也就不会有人格,而没有人格的社会往往是缺乏良知的。没有良知,何来真诚?缺少良知,没有真诚,这样的社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恐怖的。